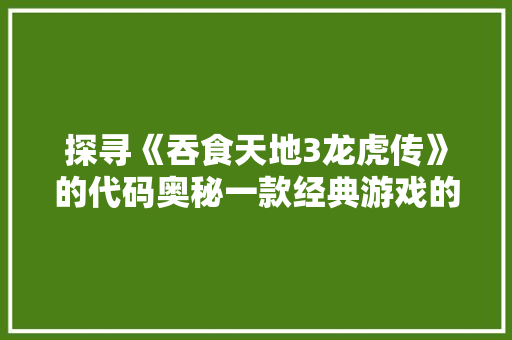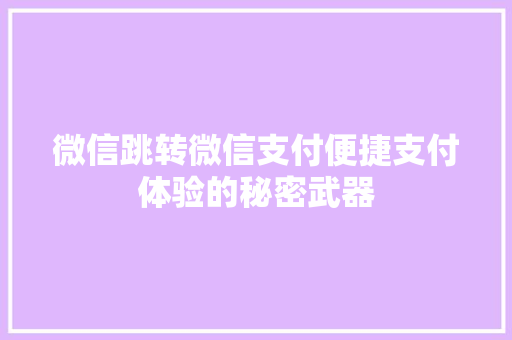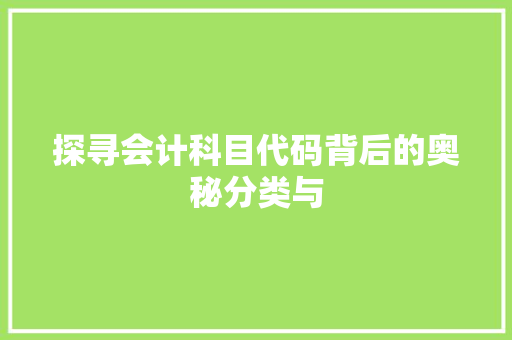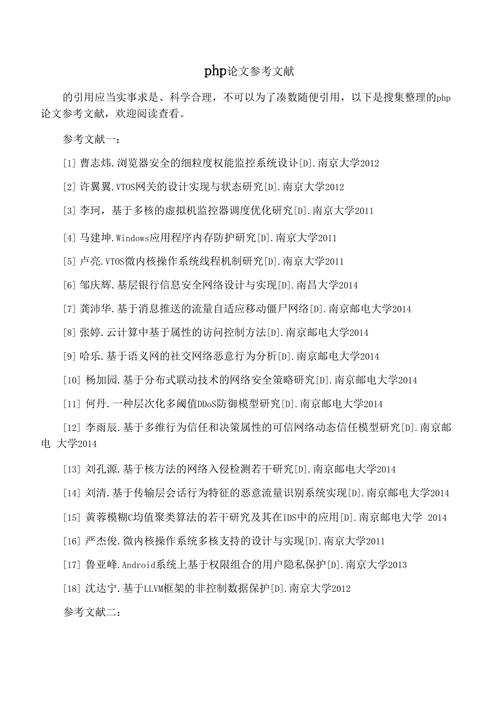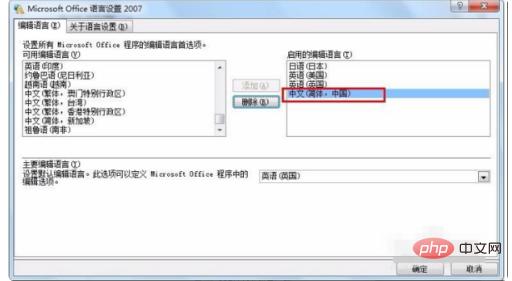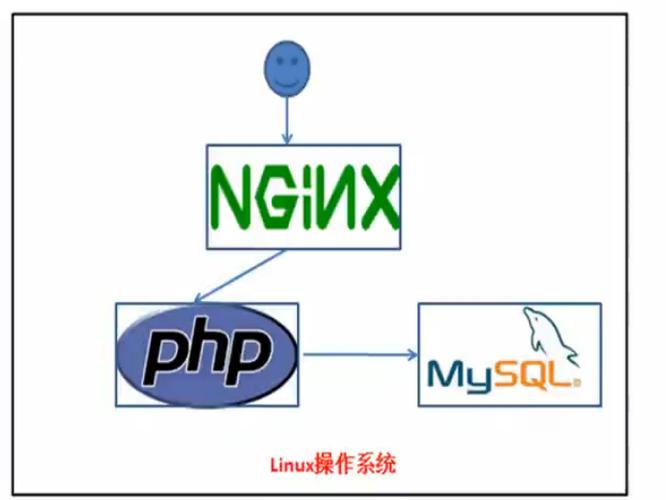在既有成果根本上,我们有必要系统总结“殷金文的特色”,使之理论化并自成体系,以便更好地辅导金文整理和研究事情:一是要透过征象看实质,即看到族徽、日名、战役、赏赐等表面征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其背后的社会成分与文化制度;二是要紧密联系殷文明的内涵,如殷人重视敬拜先王先妣与家族先人的文化特性,如通过赏赐来掩护王朝统治的政治机制;三是要看到殷金文透露的独特社会信息,如子与小子之间的宗法等级关系。基于以上理念,本文从社会组织、国家形态、文化特性等三个方面,来宏不雅观核阅殷金文的特点,将干系认识从标签化(如族徽、日名、战役、赏赐)提升到理论化,期待能进一步加深对殷文明的理解,更好认识周初继续殷制的历史状况。
一、晚商王朝社会组织的印记

(一)家族标识:族徽(族氏铭文)

贵族家族是殷代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学界主流见地认为,殷金文中的族徽(族氏铭文)是家族标识。[7]曹大志师长西席则认为“族徽”是作器者署名,是支属、职衔称谓,可备一说。[8]我们并不认为,族氏铭文是作器者个人标记。殷代与西周早期,均有不同贵族个体利用同一族徽的例证。如西周早期,作册夨令诸器(4300、4301、6016、9901)与作册大方鼎(2758-2761)记载,[9]作册夨令、作册大分别做事于周公、召公家族,其族氏铭文同为、,可见二人出身于同一史官家族。这个族徽,学界一样平常释作“鸟丙册册”,[10]属于复合型族徽,其下的丙形,有的作冉(或释冈),如、。[11]严格说来,族徽只是家族标记,并非殷代记录措辞的通用笔墨,学者仅是为研究的方便,权且将之释作干系笔墨。
(二)家族先人:日名
殷代贵族制作铜器,其动机是敬拜家族的先人,故会铭记祖、妣、父、母、兄等去世者日名。日名如何产生,众说纷纭,[12]我们主见“祭日说”,即是为了敬拜去世者而选定的。殷代周祭制度中,日名与祭日天干相同。[13]殷墟卜辞中的祊祭和岁祭,日名和祭日天干,也是对应的。[14]殷金文中的日名,代表着作器者家族内部的主要敬拜工具,也可视为其家族印记,无庸赘述。
(三)族长:子、小子
殷金文所见贵族家族的族长,最主要的是“子”与“小子”。林沄师长西席指出,子在商代是世袭贵族的尊称,多子是商王朝的“同姓族长”。[15]朱凤瀚师长西席赞许林师长西席之说,认为子是商代宗族长的尊称。[16]至于“小子”,学者一样平常认为其身份是分支家族的族长或家长。[17]殷金文中常见“子令小子”(5417)、“子赏小子省”(5394)、“子赐小子(射)王赏贝”(2648)的材料,记载小子听命于其家族的大族长“子”,而子又听命于王,子成为商王、小子之间承上启下的主要阶层,堪称是商王朝的社会支柱。在商王朝中“子”的地位很高,而“伯”紧张是对敌对方国首领的称呼(方伯),地位就比较卑微,我们曾概括为“重子而轻伯”。[18]利用殷金文研究晚商王朝的社会与国家,子与小子是非常关键的两个社会群体,不可忽略。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辨识个别不甚清晰的拓片材料,精确考释其笔墨,如5965(铭11751)载“子光赏小子啟贝”,[19]个中“小子”之“小”字拓印不清,学者或有误读,但节制了殷金文中常见“子赐(赏)小子贝”之征象,就能精确释读。
二、殷代国家形态的痕迹
殷金文中有关当时国家形态的记载,可分为商王及王室成员、王朝职官、政治运作机制三个方面来论述。
(一)王与王室:王、王妇、王子
殷金文所见的王、王妇(妇某)、王子(子某),是居于商王朝“社会金字塔”顶真个王室成员。商王地位崇高,位居其他贵族之上,殷金文屡见商王宴饗、赏赐贵族、征伐敌方的记载,如尹方鼎[20](2709)有“王饗酒”“(王)赏贝”“王征井方”的记载。商王与周王比较,有三点显著差异:一是商王从不称“天子”,周王又可称“天子”,如伯姜鼎铭有“天子万年”(2791);二是殷先王称日名,而周先王称谥号,如文王、武王、康王、昭王之类,见于墙盘(10175)与逨盘铭文[21];三是商王自作器罕见,周王则有自作器,如周厉王自作的㝬簋(4317)、㝬钟(260)。
殷代王后,在殷墟甲骨文和殷金文中称作“王妇”或“妇某”(“某”是人名)。当然,商代出土文献中的妇,也有贵族家族之妇,如族的妇(2403),殷墟子组卜辞中的“雷妇”(《合集》21796)等。[22]殷金文中最具代表性的王妇,即殷墟M5墓青铜器铭文中的“妇好”,是武丁的配偶。[23]此外,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妇妌”,也涌如今殷金文中。[24]到了西周时期,同姓不婚制度通畅,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贵族女性人名中必须包含姓,如姬、姜、姒、姞、媿等,[25]殷代贵族女性称妇的制度就不复存在了。
殷代王子,在殷墟甲骨文和殷金文中一样平常称作“子某”(“某”是人名)。我们已指出,殷墟卜辞称作子某的王子,实际也兼有族长(宗子)和王臣的身份。[26]殷墟非王卜辞中,也有子某,则不一定是王子,有学者认为是贵族家族的子辈。[27]殷墟M18墓出土铜器铭文中的“子渔”,即殷墟卜辞中“子渔”,是商王武丁的儿子。[28]此外,殷金文中“子某”,有的可能是族氏铭文;“妇某”除王妇(王后)外,也有其他贵族之配偶,严志斌师长西席已做了较全面的统计,可以参看。[29]
(二)官制:小臣、寝、作册、
殷金文中的职官,与西周金文所见“公”、“三有司”、“师氏”、“史”组成的“司师史”体系[30]不同,独具特色。殷金文中常见的小臣、寝、作册、,都是殷王朝的范例职官,虽然他们之间分工、统属关系不甚明确,[31]有必要进一步稽核和探究,但这些职官反响了殷王朝的国家特色,可看作殷文明的标识。
小臣是殷王朝官制的突出特点,[32]西周早期继续殷制,亦设置小臣,[33]故殷及西周早期金文中常见小臣作器。殷金文中的小臣,最有名者可举小臣俞,小臣俞犀尊(5990)失落盖,族徽已不可知,铭文记录了商王(帝辛)赐贝。
寝是殷王朝特有的职官,“寝”后常连着其私名,也有学者据寝鱼爵(铭8582)等材料指出,寝某之某或为族名。[34]寝为商王近臣,可代王处理政务,权力很大,如作册友史鼎载“王令寝省北田四品”(铭2313),[35]即解释寝可巡视王朝农田。入周往后,寝官随着殷王朝的灭亡而消逝。
殷金文中的,也是晚商较常见的职官,李学勤师长西席曾论是执戈拱卫之臣,[36]不过学界尚有不同见地。[37]周初继续殷制,仍有臣。也便是说,作为殷金文的特点之一,在周初金文中也可看到。殷代之也兼有族长的身份,有其小子,如“赏小子夫贝二朋”(5967)。
作册是殷代范例的职官,其详细职掌不明。王贵民师长西席认为,作册是司理典册和册命的职官,是史官的起源。[38]白川静师长西席认为,作册是掌祝告的官,[39]他指出作册起源于为宗教性仪式中制作文辞之官;作册是殷代主要职官,周初作册连续由殷人担当。[40]殷金文记录,商王常给作册赐贝,如作册般甗(944)载:帝辛征伐人方归来,赏作册般贝。作册豊鼎铭(2711)载:商王至作册般“新宗”(即新庙)[41],赏作册豊贝。殷墟卜辞有祖甲旧宗(合集30328,无名组),新宗与旧宗相对而言。作册豊是作册般之子嗣,可证殷人作册世袭之制,商王亲临作册般宗庙,也反响对其家族的看重。
西周早期,由殷人家族世袭的作册,仍是当时政治、礼仪活动的生动群体。作册在王朝任职,并做事于姬姓强族,如作册夨令做事于周公家族(9901),作册大做事于召公家族(2758-2761),作册疐做事于康侯家族(2504)。作册要参王朝的重大礼仪,如作册夨令尊宜[42]于王姜(4301),即前往王姜处,陈设礼器俎案来敬拜鬼神;作册还会接管天子及王后之命,处置对外事务,赏赐诸侯,或安抚周边部族,如王姜(王后)命作册睘安夷伯(5407、5989),周王命微史家族的作册旂给相侯赐土(9303、9895),其职责并不限于祝告鬼神。西周中期往后,作册群体逐渐消逝在政治舞台上。综上,虽然作册群体屡见于西周早期金文,但这一职官产生于殷代,仍是殷文明在政体方面的主要特点之一。
(三)政治机制:赐贝(赏贝)、蔑历
殷周金文是研究殷周政治制度的第一手宝贵材料。西周中晚期政治机制中最主要的环节——册命制度,便是学者利用金文材料,才得以揭示和深入认识的。[43]本文认为,殷金文中常见的“赐贝”或“赏贝”,如商王赐小臣俞夒地之贝(5990),又如氏之族长(子)赏其小子贝(5417),便是和西周册命制度相似的政治机制,是殷王朝掩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主要政治工具。
首先,在殷王朝的政治性赏赐中,赐贝是最普遍的仪式。据统计,赐贝(或赏贝)铭文占殷代赏赐类铭文的80%,有41例。[44]其他赏赐物较罕见,有玉、积、豕、户、釐,约10例,这些赏赐物比较驳杂,且各自数量很少,基本一见,无法充当仪式或制度中的通用物品。
其次,作为政治赏赐物的贝,在殷代并非货币,而是具有象征意义,有彰显受赐者家族茂盛光彩的浸染。[45]殷金文所见其他零散的详细赏赐物,均无象征意义,如“湡积五年”(2653)是指五年农业收成。“丐”跟在“赏贝十朋”之后(9894),则明确是在赐贝仪式中被赐予的。赐釐(5396),涌现于“归祼于我多高”的敬拜场合。此外,“户”似为贝之定语(4144)。明确是商王赏赐贵族玉、璋的只有一例(3940)。族长(子)赏赐下属玉璧也有一例(5373),另有其赐作册、的一例(5373)。此三例赐玉,其数量无法与40多例赐贝比较,也应归为详细赏赐物之列。
第三,西周王朝在早期继续赐贝制度,并沿用至穆王之世,周天子、王后、和内外服诸侯均有赐贝之举。如王赏燕侯旨贝廿朋(2628),王赐德贝廿朋(2661),王姜赐作册夨令贝十朋(4300),周公赐贝百朋(2739),燕侯赐圉贝(2505),康侯赐作册疐贝(2504),其例甚多,不一一列举。
总之,殷金文常见赐贝之例,不能大略视为一样平常性赏赐,应认识到这是一种确认与强化贵族之间高下级统属关系的一种政治机制,并深刻影响到西周王朝早期的统治。
殷代与赐贝制度干系的是“蔑历”,张懋镕师长西席已指出蔑历是殷式词语,[46]我们据小子卣铭(5417)中赏贝与蔑历并见的记载,可进一步将蔑历视为与赐贝配套的政治仪式活动,晁福林师长西席则将蔑历详细定义为口头勉励制度。[47]虽然,目前殷金文所见蔑历,仅有一例,但蔑历一词及其干系制度,肇端于殷代,是客不雅观事实。西周王朝早期继续殷制,保留蔑历之制,并沿用至西周中期前段穆王之世前後。我们预测,今后如再创造新的长篇殷金文材料,应还会再涌现蔑历的记载,且很可能是与赐贝并见的。
三、殷代文化的特性
殷金文的内容,除了族徽、日名、人物、赏赐(赐贝),剩下部分有两个重点:一是青铜器的自名,二是历日信息。这两个重点,都具有很强的殷文化特性。
(一)铜器自名:彝、尊彝
容庚师长西席指出:“商器铭文简质,不著器名,只称共名曰尊,曰彝,曰尊彝。今之所见,以酒器为多。”[48]张光直师长西席认为,尊、彝、宝彝、尊彝、宝尊彝等自名属于通用名,实际对应食器、酒器、水器等器形;另有一些自名与器形干系,如车彝、旅彝等多指卣,叫从器的都是食器,偶有酒器。[49]本文以两位师长西席见地为根本,依据史语所“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和严志斌师长西席《商代青铜器铭文总表》[50],进一步稽核、剖析殷代青铜器自名问题。
1.殷代青铜食器、酒器、水器均普遍自名为“彝”,以鼎、簋、觚、爵、卣、尊、觯居多。但未见兵器、乐器。详细说,食器类型有:①鬲(741)、②甗(867、铭3239)、③鼎(2013、2124、2125、2139、2245、2425、2709、新172、新626、新1565)、⑤簋(3434、3435、3457、3940、3990、新141、新170、铭4536);
酒器类型有:①卣(5148、5167、5171、5205、5215、5292、5293、5294、5367、5375、5377、5417、10562、新1092)、②尊(铭续790)、③觯(6474、6481、6485、6496)、④觚(7287、7302、7303、7311、新1065、铭9778)、⑤爵(8509,9088、9101、新106、新848、铭8466)、⑥角(9102)、⑦斝(9235)、⑧觥(新184)、⑨方彝(9877、9894)、⑩壶(9544);
水器有:盉(9404、9415)。
2.殷代青铜食器、酒器有少数自名为“宝彝”。食器类型有:鼎(2459)、簋(3665、4144);酒器类型有:卣(5394、新1387、新1588)、觚(7301)、觥(9301)。
3.殷代青铜食器、酒器、水器普遍自名“尊彝”,以鼎、簋、卣、尊居多,爵、盉也较多,酒器整体数量大。未见兵器、乐器。详细看,食器类型有:①甗(886、917、922)、②鼎(2311、2328、2335、2403、2594、新924)、③簋(3601、3604、3625、3717、3861、4138);
酒器类型有:①卣(5114、5186、5238、5202、5211、5238、5266、5280、5285、5338、5349、5350、5351、5375、5380、5414、铭12194、铭13082)、②尊(5794、5840、5893、5894、5926、5935、5936、5965、5967、5971、新1663)、③觯(6484、6505)、④觚(7288、7306、7312)、⑤爵(9072、9090、9092、9093、9098、铭8574)、⑥角(9042、9100、9105)、⑦斝(9246、9247、9249)、⑧觥(9294、9295、9298、铭续893)、⑨罍(9818、9819、9820、新1377)、⑩方彝(9883)、①①壶(9550、9576);
水器类型有:盉(9402、9421、9422、铭14684、铭14766)。
4.殷代青铜食器、酒器有少数自名“宝尊彝”,多为鼎、卣。食器类型有:鼎(2532、新923、新1566);酒器类型有:卣(5281、5321、5360)、尊(新1794)、觚(7307)、觥(9291)。从目前材料看,宝尊彝之称在西周早期更为盛行。
5.殷代青铜器极少自名“䵼彝”,目前所见3例均为食器,为同一家族所作,即:甗(891)、鼎(2137、2138),其铭相同:“作妇姑䵼彝。”
6.殷代青铜器自名“从彝”者只有一器:光斝(9237)。
7.殷代青铜器自名“宝尊旅彝”者仅一见:卣(5362)。
8.殷代青铜器自名有“盟彝”者,仅一见:鼎(2018);有“同彝”者,仅一见:卣(5353)。盟,有敬拜义,或说即血祭。[51]同彝之同,或释凡,本文从王子杨师长西席之说释同。[52]今按:“同”为彝之义符,殷代笔墨也有从同从爵、从同从斝之字。[53]同作为义符,或指酒器,近出内史亳觚(铭9855),自名为同,[54]当与此有关。当然,仅据内史毫觚之孤证,将觚的传统分类名称,改称为同,并欠妥当。
据以上统计,殷代青铜食器、酒器、水器,普遍自名“彝”或“尊彝”,也有少数称“宝彝”、“宝尊彝”。殷器自名“䵼彝”、“从彝”也极少,也无明确自名“宝从彝”、“旅彝”、“从旅彝”者。可见在殷人的不雅观念中,祭祖所用铜器并不重视某一个体、或某一种类,而是将食器、酒器、水器作为整体来看待的。这一认识,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殷人的敬拜礼仪。
西周早期,周王朝继续殷制,贵族所作铜器,也普遍自名为“彝”“尊彝”,但“宝尊彝”之称较殷代更为普遍,具有断代标准之浸染。从西周中期开始,殷制衰落,作器则改称其专名。凡言“作宝尊彝”的铜器,其时代下限,在西周中期之前,最晚在穆王之世。
(二)历法:大事纪时、周祭纪日
殷王朝历法的特点,如大事纪时、周祭纪日,也成为辨识殷金文的主要标准。容庚师长西席附和马衡师长西席确定“商器”的四个标准,[55]即:
1.贩子之纪年月日,必先书日,次书月,再次书年,而书月必曰“在某月”,书年必曰“惟王几祀”。
2.贩子祀其祖妣,必用其祖若妣之名之日;其妣皆曰,其祭名或谓遘。
3.贩子敬拜之名有曰“日”,曰“肜日”者。
4.甲骨文恒见征人方之事,而《般甗》曰“王徂人方”;《艅尊》曰“惟王来征人方”。
马衡师长西席上述4个标准,本日概括起来可归入大事纪时、周祭纪日两大方面。而“唯王几祀”也见于西周期间,如厉王时的㝬钟(358)就铭有“唯王五祀”。殷金文中大事纪时,紧张是帝辛征人方、征井方的事宜,有纪年之浸染。如小臣俞犀尊(5990)云“唯王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在帝辛十五年。容庚师长西席补充马衡说,举例的尹方鼎(2709),铭末曰“唯王征井方”,即以征井方之事纪年。
周祭纪日,从广义上看也属于大事纪时,但殷末周祭逐日举行,周而复始,殷金文所见周祭某位先王或先妣的材料,紧张为了更准确地记录干系事宜发生的日期。如殷末寝孳方鼎(铭2295)曰“在十月又二,遘于祖甲日,唯王廿祀”,即清晰记载了“王赐寝孳赏”的甲子日在周祭中的日次,个中的“遘”并非祭名,有“遇”之义。周祭纪日的材料常有省略,如小臣俞犀尊(5990)的“唯王十祀又五肜日”,省去了月份与敬拜工具。
殷金文所见周祭的名目,仅有日、肜日、明天将来诰日,而从无“祭”与“”,而殷墟甲骨卜辞中五种敬拜是完好的,其缘故原由尚待磋商。上文已例举日、肜日的材料,明天将来诰日材料如亚鱼爵(铭2201)的“在六月,唯王七祀明天将来诰日”。此外,周祭是殷王朝特有的常祀制度,周王朝建立后旋即破除,故周初金文历法虽沿用大事纪时的做法,如簋(铭5136-5137)“唯八月公年”等例,但再无周祭纪日的材料了。
小结
本文从社会、国家、文化三个层面,论述了殷金文的特色体系,重在揭示殷金文背后的社会形态、政体机制与文化制度,如子与小子反响的家族组织,赐贝的政治仪式,周祭在历法中之运用,等等。殷周金文所见殷周文化异同,学界历来重视,我们在张懋镕师长西席强调“日名”、“族徽”之外,为磋商殷周文化之异同,增加了“子与小子”、“赐贝”、“寝”(官)、“作彝”、“作尊彝”、周祭纪日等新的视角与标准。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殷周文化之差异,不能大略地视为殷、周二代之差异,或殷、周二族文化的不同,由于西周早期至穆王之世,周王朝继续殷制,殷金文中的诸多特色,如族徽、日名、赐贝、小臣、作册、作尊彝、大事纪时等征象,也保存在西周早期金文中。由此可见,虽然王国维师长西席曾云:“中国政治与文化制度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56],然据考古、古笔墨材料来看,殷周制度的重大转变,紧张还是涌如今穆王往后。[57]
附录:金文著录书简称表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不写书名,只写编号)
2.钟柏生、陈昭荣、黄铭崇、袁国华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简称“新”)
3.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简称“铭”)
4.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简称“铭续”)
注釋
[1]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67、82页,燕京学报专号之十七,1941年。
[2] 李学勤:《青铜器入门》,第34-36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
[3]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6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4] 陈絜:《商周金文》,第161-177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5]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6] 张懋镕:《试论商周之际字词的演化》,《西部考古》第四辑,2009年。后收入《古笔墨与青铜器论集》第3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7] 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王长丰:《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雒有仓:《商周青铜器族徽笔墨综合研究》,黄山书社,2017年。
[8] 曹大志:《“族徽”内涵与商代的国家构造》,《古代文明》第12卷,2018年。
[9] 本文引用金文材料的著录书,均利用简称,详见文末附录。
[10] 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笔墨独特的表现形式》,载《陕西师范大学古代文献研究论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页。后收入《古笔墨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第240页。
[11] 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1075页。毕秀洁:《商代金文全编》,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319页。鸟丙之丙,可能是冉(也便是鱼)的变形。
[12] 张富祥:《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3-4页。
[13]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14]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0-41页。
[15] 林沄:《从子卜辞试论商代家族形态》,《古笔墨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323、329、333页。
[16]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17] 关于“小子”的身份,裘锡圭师长西席认为是小宗之长。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17辑,中华书局,1983年。《裘锡圭学术文集·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第130至132页。严志斌曾对商周金文中的小子,有较全面的稽核。严志斌:《关于商周“小子”的几点意见》,《三代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04年。
[18] 刘源:《殷墟甲骨卜辞与〈左传〉中“子某”之比拟研究》,李宗焜主编《古笔墨与古代史》第五辑,台北:“中心研究院”历史措辞研究所,2017年,第80-81页。
[19] 《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的释文是精确的,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05965。
[20] 此器异称较多,如称“邐方鼎”,也有人称“乙亥父丁鼎”,今据其作器者为尹,故采取尹方鼎,或尹鼎的名称。也有学者认为作器者是“尹光”,我们认为“光”为副词。
[21] 刘源:《逨盘铭文考释》,《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2] 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8-69页。
[23] 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文物》1977年第11期。
[24] 李学勤:《谈新涌现的妇妌爵》,《文博》2012年第3期。
[25] 李峰:《周代的婚姻与社会网络:青铜器铭文所见女性称名原则之稽核》,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26] 刘源:《殷墟甲骨卜辞与〈左传〉中“子某”之比拟研究》。
[27] 林沄:《商史三题》,台北:“中心研究院”历史措辞研究所,2018年,第61、64页。
[28] 郑振喷鼻香:《安阳小屯村落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第516页。
[29]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第205-247页。
[30] 刘源:《从韩伯豐鼎铭文看西周贵族政体运作机制》,《史学集刊》2018年第3期。
[31] 王贵民:《商朝官制及其历史特点》,《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17页。
[32] 王贵民:《商朝官制及其历史特点》,第118页。
[33] 石安瑞:《论西周金文中的小臣及其职务演化》,《北大史学》第2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34] 陈絜:《从商金文的“寝某”称名形式看殷人的称名习俗》,《中原考古》2001年第1期。
[35] 按:据铭文和族徽来看,作器者应为作册友史,故本文重新命名此器为“作册友史鼎”。
[36] 李学勤:《富商至周初的与臣》,《殷都学刊》2008年第3期。
[37] 王进锋:《臣、小臣与商周社会》,上海公民出版社,2018年,第140页。
[38] 王贵民:《商朝官制及其历史特点》,第112页。
[39] 白川静(郑清茂译):《作册考》,《中国笔墨》第39册,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1971年,第4377页。
[40] 白川静(郑清茂译):《作册考》(续),《中国笔墨》第40册,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1971年,第4489-4490、4503页。
[41] 裘锡圭师长西席认为,作册般新宗,大概指宗族。他将铭文中表示“至”的字,释读为毖,阐明为敕戒镇抚。裘锡圭:《释“柲”》,《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4页。
[42] 殷墟历组卜辞载“尊甗于父丁,宜三十牛”(《合集》32694),指放置铜甗、宰牛陈肉于俎上来敬拜武丁,有助于理解尊宜。
[43] 学者研究西周金文所见册命制度的成果颇丰,代表作是陈汉平专著。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
[44]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第338页。
[45] 柿沼阳平:《殷周时期的海贝文化及其特点》,《甲骨文与富商史》新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6] 张懋镕:《试论商周之际字词的演化》。
[47] 晁福林:《金文“蔑曆”与西周勉励制度》,《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48]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燕京学报》专号之十七,1941年,第20页。
[49] 朱凤瀚师长西席重视此研究结论,专门着重引用。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50]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第370页。简称为“严表”。
[51] 张世超等编:《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1719页。于省吾主编:《甲骨笔墨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第2638页。
[52] 何景成编:《甲骨笔墨诂林补编》,中华书局,2017年,第691页。
[53] 王子杨师长西席已指出甲骨文有从同从爵,和从同从斝之字。何景成编:《甲骨笔墨诂林补编》,第696页。
[54] 王占奎师长西席认为,据内史毫觚,觚应改称为同,同来源于竹筒。王占奎:《读金随札——内史亳同》,《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55]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30页。
[56]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不雅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
[57] 曹斌:《恭懿之际西周国家的转型》,《中国公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