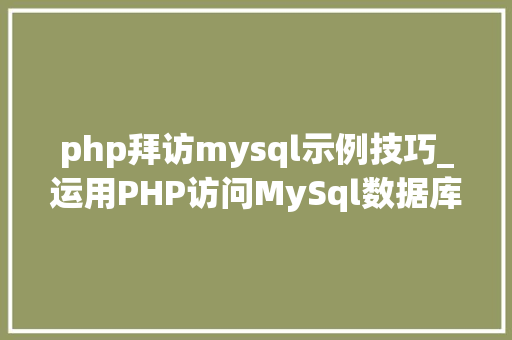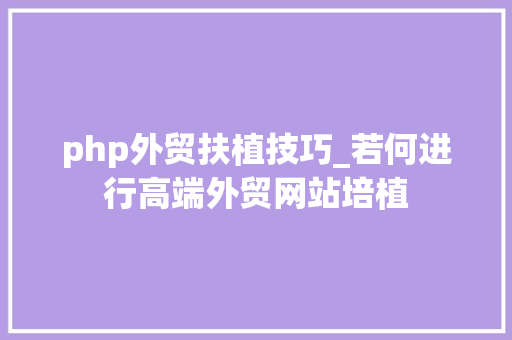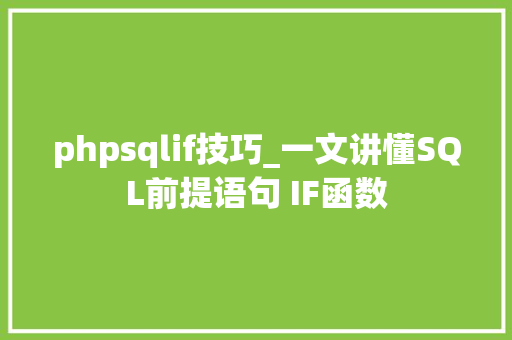2024年,恰逢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师长西席诞辰130周年,也是其访美演出94周年。1930年,梅兰芳师长西席以中国艺术家的豪情与气概,带领中国京剧赴美演出,首创了中国戏剧登上天下历史舞台的序幕。从1930年梅兰芳访美开始,梅兰芳这个名字就不仅是中国的,同时也是天下的。
梅兰芳不仅轰动美国艺术界,乃至在访美之后几年中,仍有美国艺术评论家对其进行评述。他将中国戏剧特殊是京剧艺术推向天下,自此天下对中国戏剧的研究,特殊是梅兰芳的研究就从未停滞过。不仅有访美期间,美国各报刊杂志的艺术评论,一些外洋学者乃至开始关注梅兰芳,涌现先容梅兰芳和中国戏剧的英文专著。进入21世纪以来,外洋学者对梅兰芳的研究更加深入和专业,出版了大量著作,特殊是近二十年更有数量弘大的期刊文献揭橥有关研究梅兰芳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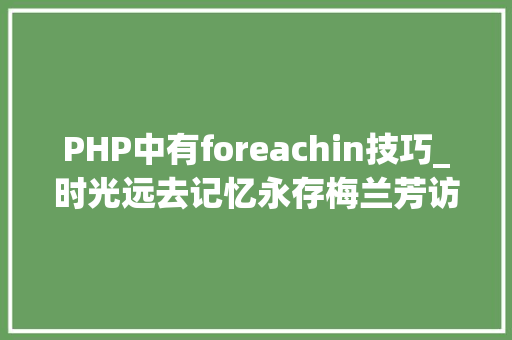
有人说:“梅兰芳是20世纪中国戏剧的一个奇迹,他的思想须要系统研究,他的造诣值得负责总结,他的弯曲经历,更是我们认识时期变迁的主要窗口。”因此,重温历史,理解外洋学者对梅兰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客不雅观而全面地研究梅兰芳和梅兰芳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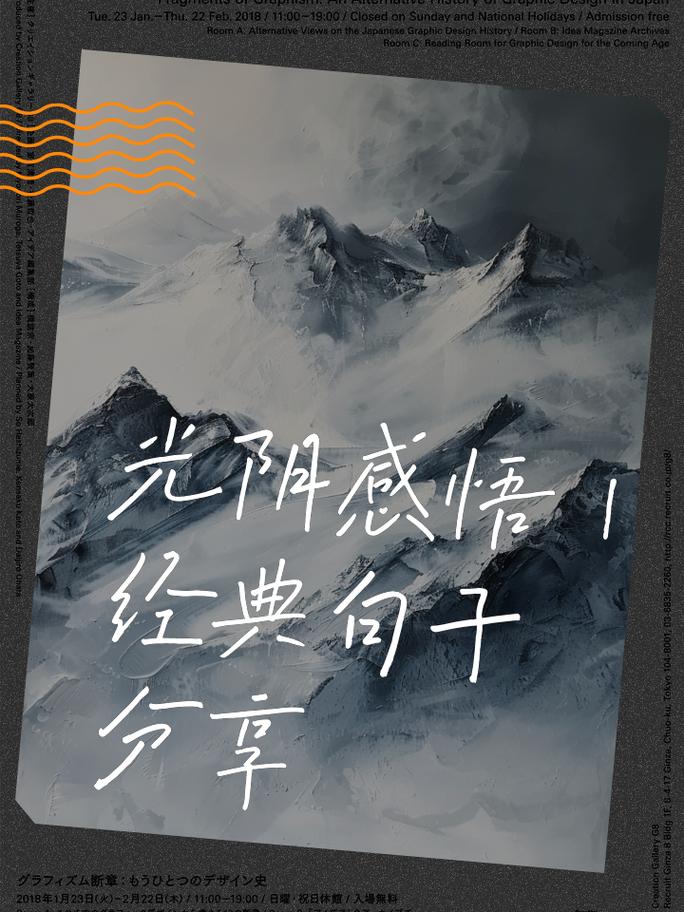
访美演出
众所周知,梅兰芳师长西席的访美演出预备许久,除经费问题外,如何向美国不雅观众宣扬京剧是梅兰芳和其团队考虑的头等大事。在预备过程中,智囊团的核心成员齐如山师长西席为梅兰芳访美演出编写了四本先容性书本:
第一本是《中国剧之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Opera),个中包括声腔、舞蹈、演出、服装、盔头、胡子和髯口、道具、配乐等八部分内容;
第二本《梅兰芳》,包括梅兰芳家族史、旦角的起源、中国戏剧中的旦角、梅兰芳的艺术、梅兰芳艺术在中国戏剧的地位、他在中国的声誉、他的国际荣誉等七部分内容;
第三本为《梅兰芳笙歌谱》(Mei Lanfang’s Singing),专门先容中国戏曲的演唱,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戏曲中的唱是西方人最难明得的部分,因此将戏曲的公尺谱翻译成西方乐谱;
第四本是《剧目解释书》,除简要先容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还对故事中要演出的部分和意义进行了详细解释。
以上四本书均被译成英文并印刷成册,方便美国不雅观众和文艺界更好地理解与欣赏中国戏剧。
除笔墨资料外,还有两百多幅图片同样配有英文先容,这些宣扬资料为梅兰芳访美演出起到了主要浸染。
在访美演出过程中,美国媒体对梅兰芳的演出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评价。
在纽约的第一晚演出后,1930年2月17日,《纽约天下》(New York World) 对梅兰芳前一晚的演出进行了宣布。文章认为“只管对公元前200年或是更久的戏剧背景一无所知,只管有数百种舞台规范和手势,只管情绪代价不雅观与你完备不同,只管音乐伴奏常常会让你的耳朵不舒畅,但你仍旧会时时时被它迷住。”“只要他站在舞台上三分钟,你就会承认,梅兰芳是你见过的最精彩的演员之一。他集演员、歌手和舞蹈家于一身,使你永久看不到这三种艺术之间的界线,事实上,这三种艺术在中国戏剧中是不可分割的。”
同一天,《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宣布中说到,梅兰芳带来的京剧和他们所熟习的西方戏剧没有相似之处,但与一门完备异国情调的艺术比较,措辞的障碍微不足道。作者认为中国戏剧风格独特,具有程式规范,且历史久远。如果抛开它的不同与新奇,欣赏它的程式动作和精美衣饰,你会隐约感到自己在触碰几个世纪而形成的陌生且成熟的戏剧。“大概你乃至会有少焉痛楚的反思,虽然我们的戏剧形式也足够生动,但在想象方面从来没有像中国戏剧这样自由。”
梅兰芳在纽约首演之后,美国媒体纷纭争相宣布。1930年2月20日,《纽约天下》(New York World) 刊登了William Bolitho的宣布,他首次提出“在第49街剧院演出的梅兰芳,无疑是本季纽约艺术演出的最高峰之一。”他认为梅兰芳首先是舞者,而且是最高水平的舞者。如果要像运动员那样排名的话,在世界顶级戏剧家中,梅兰芳是霸占一席之地的。
梅兰芳在芝加哥和加州的演出同样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1930年4月1日,《芝加哥逐日论坛》(Chicago Daily Tribune) 宣布了梅兰芳的演出,标题为“中国演员在公主剧院赢得赞誉”(CHINESE ACTOR WINS APPROVAL AT PRIINCESS THEATRE)。文章把中国古典戏剧比作一个人第一次看到一幅俏丽的画作,却不知道个中隐蔽的含义,他觉得到了美,但画的深意远超过了它外表的颜色。
访美意义
梅兰芳访美演出的成功极大鼓舞了中国的有学之士,唤醒了学人的文化自觉,开启了中国近代戏曲翻译的高潮。
20世纪30年代,正在英国深造的熊式一,在多位教授的鼓励下,改写了中国传统戏剧王宝钏的故事,创作了英文话剧《王宝川》(Lady Precious Stream)。该剧在英国演出大得胜利后,次年秋登上纽约百老汇的舞台。《王宝川》英译本自问世以来,一贯是中外学者和戏剧家研究的热点,它的主要浸染和意义,正如英国雷丁大学的 Ashley Thorpe 博士所说,“这出戏(《王宝川》) 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第一部被中国学者译写、导演并且搬上伦敦舞台的中国传统戏剧”。
20世纪30年代,大量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创办英文杂志,努力构建中西文化的桥梁。1935年8月,创刊于上海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 1935-1941) 应运而生,刊名源自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念,表达了创刊者广博的文化视野与胸襟。
当时《天下》的编辑与作者群聚拢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文人学者,其“评论”专栏刊载了大量有关中西文化评论的文章,钱钟书的名篇“中国旧剧中的悲剧”(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姚莘农的“元杂剧的主题与构造”(The Theme and Structure of The Yuan Drama) 和“昆曲艺术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un Ch’u) 就揭橥于此;而“译文”专栏凑集了当时国内外精良的汉学家与译者,揭橥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译作,林语堂所译清朝沈复的《浮生六记》(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多期连载,姚辛农的译作《贩马记》(Madame Cassia) 和《打渔杀家》(The Right To Kill) ,以及英国汉学家Harold Acton 所译的《春喷鼻香闹学》(Ch’un-hsiang Nao Hshueh)、《狮吼记》(Scenes from Shih Hou Chi) 和《林冲夜奔》(Lin Ch’ung Yeh Pen) 均揭橥于此。
在中国近代史上,传统戏曲剧本翻译的高峰期,以及对中国戏曲的英文评论险些都揭橥在《天下》,后世学者在研究中国戏曲外洋翻译时,《天下》都是不容忽略的主要文献。
此外,梅兰芳的访美演出对后来的中国戏曲外洋演出具有首创之举。特殊是张彭春通过实践总结出的外洋演出模式,直到本日对外洋的中国戏曲演出仍具借鉴意义:结合不雅观众审美和生理的剧目挑选;传统戏的保留;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对文人学者等主流群体的关照;看重媒体宣扬和艺术评论的浸染及影响;举办合营演出的干系文化讲座等。
2006年9月,由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白先勇教授策划的青春版昆剧《牡丹亭》在美国演出,也在某种程度上接管和借鉴了张彭春为梅剧团所定下的演出方案。2015年9月,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程派演出艺术家张火丁教授《锁麟囊》和《白蛇传》的访美演出,以及2016年苏州昆曲剧院的《牡丹亭》在英国演出,也同样借鉴了媒体、宣扬、评论、讲座、大学巡讲等系列活动的演出模式。
访美影响
随着梅兰芳访美演出成功,以及熊式一的《王宝川》在外洋演出的影响,外洋的汉学研究逐渐热了起来。
到20世纪中后期,国际汉学研究的中央已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受益于早期庚款留学,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大儒,在美国创办了旨在研究中国文化的一系列期刊。如中国当代著名措辞学家赵元任师长西席与美国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1969年在美国创办的“中国演唱文艺研究”,并将杂志取名为CHINOPERL,个中CHIN为Chinese, O代表Opera, PER是Performing,L则是Literature。由此可以看出创刊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初心,现在杂志不仅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进程,而且已经成为外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文献。
此外,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中国文学》)、Asian Theatre Journal(《亚洲戏剧》)等也是当代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紧张学术期刊。
美国学者对中国戏剧开始产生浓厚兴趣。
前期参与梅兰芳访美预备中,为其图谱进行翻译的美籍华人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在梅兰芳访美前后,先后出版先容性书本《梅兰芳:中国顶级演员》(Mei Lan-Fang: Foremost Actor of China) 与《梅兰芳和中国戏剧》(Mei Lan-Fang and Chinese Drama)。
在旧金山演出时,美国学者欧内斯特·K·莫(Ernest K·Moy)编纂了《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The Pacific Coast Tour of Mei Lanfang) 的英文文集。《文集》多为先容中国京剧和梅兰芳平生及艺术演出的文章,为首一篇则是胡适撰写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在文章末了胡适还特殊提到,“梅兰芳和他的朋友们为这次访问演出所准备的许多中国戏剧图表和其他阐明性资料,对研究天下戏剧艺术史发展的人士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代价”。
多年后,1935年张彭春编辑整理了梅兰芳访美期间美国报刊杂志对梅兰芳演出的评论和宣布,出版《梅兰芳在美国:回顾与评论》(Mei Lan-Fang in America: Reviews And Criticisms)。
而受梅兰芳访美影响最深确当属美国学者施高德(A.C. Scott)。他曾在20世纪50年代专门绕道喷鼻香港来到北京与梅兰芳会面,著有《梅兰芳:戏班魁首》(Mei Lan-fang: Leader of The Pear Garden)。该书以学者视角全面先容中国传统戏剧和梅兰芳。
近百年来,外洋学者对梅兰芳的研究从未间断,进入新世纪更热了起来。2009年,美国华裔学者杨富森(Richard Fusen Yang)著《梅兰芳和京剧》(Mei Lanfang and Peking Opera),该书以梅兰芳发展为主线,贯穿先容京剧知识;2010年,旅美华裔学者田民(Min Tian)出版《中国最伟大的男旦演员:梅兰芳的艺术人生》(China’s Greatest Operatic Male Actor of Female Roles: Documenting the Life and Art of Mei Lanfang, 1894-1961),这是第一本从中国、西方和跨文化的角度以及梅兰芳自己的角度论述梅兰芳生活和艺术的英文书本;作者于2012年又出版《梅兰芳与20世纪国际舞台——中国戏剧的定位与置换》(Mei Lanfang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Stage: Chinese Theatre Placed and Displaced),该书以梅兰芳的艺术造诣和影响为视角,探究其艺术的跨国和跨文化浸染。
虽然已经由去94年,但梅兰芳的访美演出仍旧意义非凡。它与一样平常的商业演出不同,而是授予了中国文人的文化自觉,更像是寻求天下戏剧舞台上的代价认同和身份认同。自此,中国戏剧走向天下舞台,外洋学者对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和梅兰芳研究,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外洋汉学的主要内容。梅兰芳,将他的名字和中国戏剧成功留在了北美这片地皮上。
本日,我们不仅回望历史,更关注外洋的“梅学”研究,外洋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海内学者的研究共同铸就着梅兰芳艺术的研究内容。在新世纪,相信梅兰芳访美的佳话,会连续续写着新的内涵和意义。(董 单)
来源: 艺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