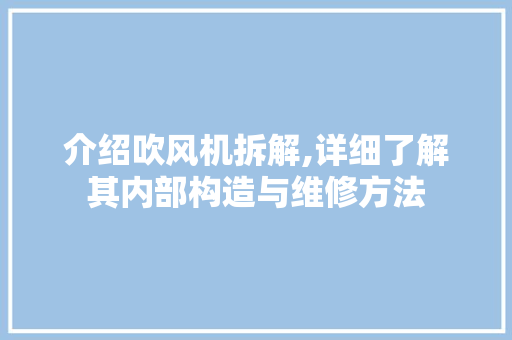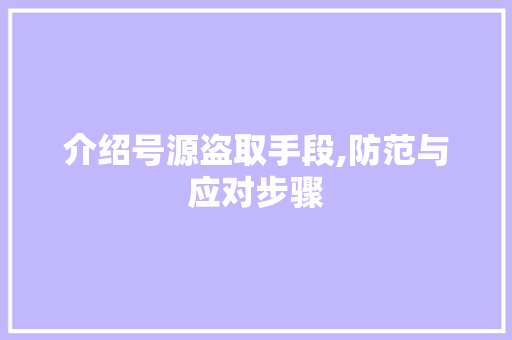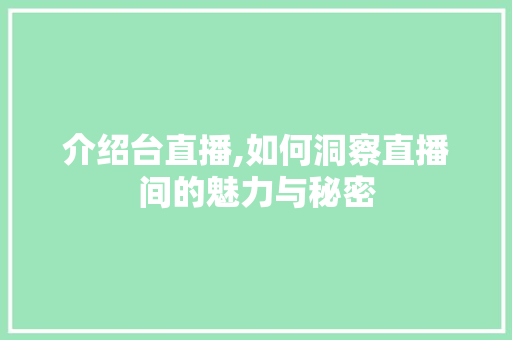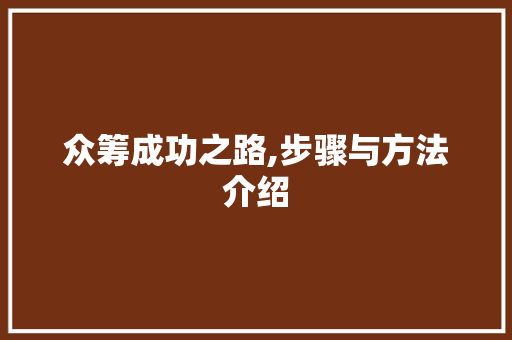[关键词]: 共情;认知传播;感情传播;传播模型;共情机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甬江社会科学青年人才帮助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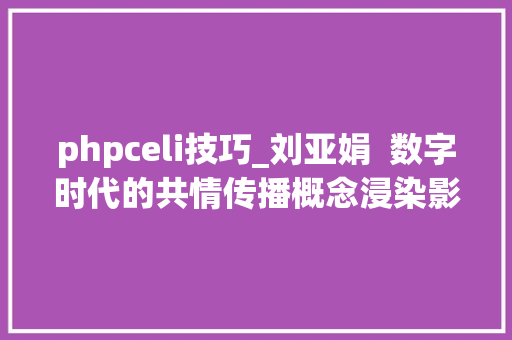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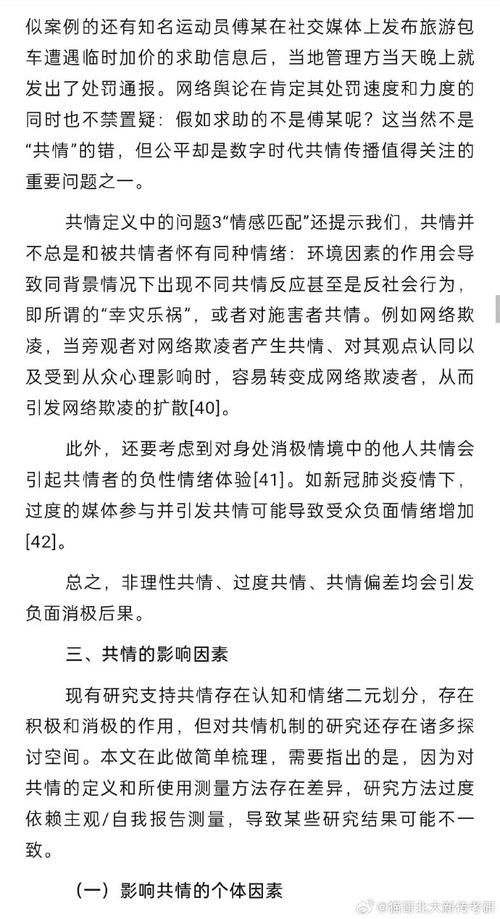
刘亚娟,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法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数字新闻、传媒伦理。
共情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巴尔扎克笔下“杀去世满大人”(tuer le mandarin)所引发的空间道德间隔谈论开始,对他者耐劳场景的“想象性的移情”成为西方同情心革命的主要话题[1];到民国时期利用媒介塑造孝女复仇形象,引发大众舆论同情民意成功免于去世刑的施剑翘[2];再到魏则西事宜、于欢案等,已深深印刻在当代新闻传播进程中。
自吴飞教授于2019年从新闻传播学角度系统阐述“共情传播”及其理论根本与实践路径后,共情传播研究数量上升、话题构成日渐丰富,中国知网学术关注度指数显示,与共情传播共同涌现的关键词频次由多至少依次为“国际传播”“短视频”“跨文化”[3]。当前数字传播已经向人类展示了丰富的运用图景,也带来大量熵增。2023年吴飞教授又提出作为数字交往新假设的“数字共通”理念,并提出其基于共享、共鸣与共通而运作,指出“共通”既要有交往理性的支持,也须要一种广泛的共情意识和共情实践[4]。共情传播的意识和实践冲破了“视理性交往为发展具有批驳性当代‘"大众年夜众’必不可少要素的做法”[2](P.10),但数字共通也面临着主体间性子疑和数字解域的寻衅[5]。
当前研究中对“共情”一词的不同内涵观点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它包括“同情”“同理”等在内的诸多观点层面及历史解读,契合了数字背景下贱传理性(专业性)未曾触及或难以阐明的部分。有人批评被感情旁边的"大众年夜众会陷入极化和偏见,也有人心甘情愿为感情代价买单。共情实质上是多维的、人际的,并受环境影响,其发生浸染的过程是繁芜的。现有大部分研究放大了共情的积极部分,共情多被用来磋商如何引发受众与传播者同向的正面情绪[6],对共情的悲观浸染涉及不多;研究多将机构媒体和政府官方作为引领共情传播的主体,忽略了多元行动主体,也少有对传播内容中被共情者的个体或群体研究。综上,共情传播目前处于共情意识有余,共情认知和实践不敷的田地。
本文环绕“共情”的观点史展开回顾,充足传播学研究中共情认知及其影响成分理论,并结合交叉学科研究进展为共情传播实践供应建议。
一、共情的观点史
目前对共情尚无统一定义,一方面是由于共情研究涉及的学科不同,生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学都有各自的研究角度;另一方面是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深入,共情理论特殊是共情的发生机制研究正在不断拓展、深化。因此,要充分理解共情以辅导实践,有必要稽核其观点史。
(一)共情的词源与观点演化
英文“共情”(empathy)源于德语名词“einfühlung”,可以直译为在自然和艺术中感想熏染各种形式和形状的能力(并将其投射到绘画、艺术工具和自然中)。这一美学观点被英美生理学家借用,便有了英文的“empathy”[7](P.9)。英语天下对共情一词的利用,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分为两条路径:一是精神病学和生理学家,将其利用在对精神病的诊断及生理治疗中;二是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将其作为一种测试工具以在访谈中更可靠地研究工具的生活史[7](P.101-115)。
二战后,共情从学术术语转变为大众词汇,共情(empathy)开始频繁涌如今英文著作中;被用在电影、文学等艺术形式评价中,广泛涌如今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涉及广告营销、社会管理、种族等话题。以至于有些学术谈论在须要用到“共情”时再次用“einfühlung”以作区分。以传播领域为例,20世纪50年代起,共情就被认为是一种有效触达受众的技能:它可以阐明为何家庭情景笑剧比单人脱口秀更具吸引力,为何电视智力竞赛和悬疑笑剧可以吸引不雅观众,广告中的主人公形象设定每每也是希望受众在媒介上找到自己[7](P.208-210)。
20世纪90年代,随着被认为是人类模拟、社会学习和共情行为的神经基质的“镜像神经元(MNS)”被创造,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认知、社会和发展生理学家以及哲学家都加入了界定共情和描述其神经根本的最佳方法的激烈辩论。由此引发了共情是天生的能力,还是一种经由演习可以达成的技能,并具有道德行质的辩论。
汉语中“共情”一词涌现比较晚,但“同情”一词历时久远。《史记·吴王(刘)濞传》有:“同恶合作,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去世。”[8](P.522)这里的“同情”指同样的“心”,含有好恶不雅观念相同的意思。汉语“共”“同”词义词性附近,常常共同涌现,如“同甘共苦”,因此“同情”是对别人的遭遇在感情上发生共鸣[9](P.345),而“共鸣”是由别人的某种感情引起的相同的感情[9](P.122),两者均强调主体感知与客体感知相同。从汉语构造上看,虽然二者都可以用作谓词,比如“共情”谁,“同情”谁,但在体词利用上,一样平常用“共情力”“同情心”,前者代表一种能力,后者形容一种感知到的感情,这也能解释二者在定义性子上有所不同。
民国期间,“同情”时常与“国民感情”“群众感情”或“舆情”混为一谈。林郁沁的考证认为,20世纪30年代“同情“已经明确指涉着作为大众传媒之接管者的城市大众的集体同情[2](P.4-5)。“舆论”一词在当时表示了理性和进步,但代表大众情绪的同情民意却被认为是女性化的、感情用事的,并且被深陷于荒谬迷信之中[2](P.6)。这与今时今日情绪和理性在传播中的浸染之争有着历史的相似性。
新中国以来,学界对共情的谈论从美学磋商开始。1980年,李泽厚《美学论集》中指出,人们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绪、意志、思想授予外物,结果彷佛外物也真正具有这种情绪、意志、思想似的“移感情化”是一种客不雅观存在的征象[10](P.26)。但美学领域的移情和生理学哲学观点的移情在主体和客体上均有差异。与本文所谈论“empathy”观点相同的汉语词汇“移情”,被认为是一种想象自己处于别人的情状并理解他人的情绪、希望、意念和行动的能力,通过移情这一中介,感情体验可以引发道德动机[11]。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移情的生理学谈论逐渐增多。2003年,马丁·霍夫曼(Martin L.Hoffman)的著作《移情与道德发展》(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在海内出版,该书系统定义了移情的发展阶段和浸染。后续在生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共情”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利用,“移情”则连续多用在美学话题中,2015年知网学术关注度上“共情”干系的中文文献量首次超过了“移情”。
新闻传播学领域,1995岁首年月次有学者采取生理学视角提出了移情能力的强弱是其采访和写作能否成功的主要成分[12]。“共情”一词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涌现同样稍晚于“移情”,其发展脉络与移情类似,零散散见于采访播音主持等传播实践剖析中。自2019年吴飞教授系统阐述“共情传播”及其理论根本与实践路径后,共情传播的研究范围、数量都有扩展,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
(二)共情的观点界定点
由于各界对共情定义尚未达成一存问见,加之各学科对“共情”一词的利用侧重不同,要穷尽共情的定义是困难的。本文通过对共情历史的梳理,结合当前共情传播中紧张涉及的生理学、神经科学和社会学领域学者对共情的观点界定,对共情观点的界定要点梳理如下。
1.共情工具:对事或对人
从德语词源看,早期的共情理论包含了对物的共情。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剖析中,移情也包含了大量对物的情绪体验。而当代神经科学和生理学研究紧张稽核对他人情感的感知/共情,这些情绪包括疼痛[13]、厌恶[14]、恐怖[15]、愤怒[16]、焦虑[17]、愉悦[18]、尴尬[19]和悲哀[20]。因此,在进行社会学和生理学谈论时,紧张指涉的是对他人的共情。值得把稳的是随着天下生态环境变革,涌现了对地球资源环境景象共情的呼吁,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能的发展,与AI共情的磋商也逐渐增多,共情观点未来是否会再次转向对物共情尚未可知。
2.共情动因:知觉或理性
20世纪初共情观点涌现时,德国“移情派”美学紧张的代表特奥多尔·立普斯(Theodor Lipps)方向于认为共情是对客体感想熏染的被动和直觉的反应。而最早将“einfühlung”译入英语天下的实验生理学代表学者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Titchener)则方向于认为共情是个体主动、努力地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在天下[21]。当代生理学家将共情定义为情绪反应,认为共情是一种源于对他人情绪状态或状况的理解的情绪反应,且这种情绪反应与他人在特定情形下的感想熏染或预期的感想熏染相似[22](P.75)。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等生物学家提出了感知-行动模型,指出对共情工具状态的把稳感知会自动激活主体(共情者)关于状态、情境的表征,除非被主不雅观抑制,否则这些表征会自动引发或产生干系的自主神经和体感反应[23]。对共情动因界定的差异构成了感情共情和认知共情的根本。
3.共景况况:情绪匹配或整体感情
所谓情绪匹配,是指共情者和共情工具具有相同的情绪体验。在对另一个人的内在状态产生认知察觉后,是会产生相同匹配的情绪,还是根据整体环境推断他人情感并进行共情,是共景况况的差异。
美国哲学教授艾米·科普兰(Amy Coplan)认为情绪匹配是共情的关键指标之一[24](P.6)。提出共情利他假说的生理学家丹尼尔·巴特森(C. Daniel Batson)也将共情定义为与他人须要的感知相同等的以他人为中央的情绪,强调情绪匹配与他人福祉的关系[25](P.41-58)。而生理学家马丁·霍夫曼则认为不一定须要匹配,“关键哀求是生理过程的参与使一个人所产生的感想熏染与另一个人的情境更加同等,而不是与他自己的情境更加同等[26](P.45)。霍夫曼举的例子是当一个人看到他人受攻击,纵然受害者感到悲哀或失落望而不是感到愤怒,不雅观察者也会感到愤怒。这里的愤怒与悲哀或失落望是一个整体,包括“对模型干系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的感想熏染”。整体感情论定义扩展了共情的范围。
总之,对共情工具、动因和状态的不同认知,构成了共情的多样化定义。这有助于我们在利用共情观点时,对主体,客体及二者互动状态进行明确区分。
(三)共情的种别
生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共情紧张分为感情共情和认知共情两种模式。由于共情观点界定和丈量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中还有积极共情、悲观共情、运动共情①平分类,这些分类总体都是环绕共情发生机制展开的,环绕这些机制尚未有统一的科学不雅观点,因此本文不引入过多分类标准以防稠浊。
感情共情是指由匹配或同感的办法直接管他人情绪的影响而对他人情绪产生的知觉,强调由他人情绪所引起的间接感情体验;而认知共情则是指通过自上而下的加工办法想象他人的感想熏染,强调对他人所处感情状态的推断和理解[27]。
感情共情紧张包括对他人的共情关怀,如在他人遭受痛楚时表现出的同情和怜悯;感情传染,如对他人痛楚产生的不适和焦虑感[28]。认知共情包括视角选择(Perspective-Taking),即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想象从他人的角度看天下,理解他们的思维和感想熏染;共情准确性:强调个体准确判断他人想法和感想熏染的能力[29](P.79-97);感情识别和调节:能够从表情动作等非措辞笔墨线索识别被共情人的情绪状态,能够共情而不被所共情的情绪所淹没。
总之,对感情和认知共情的划分,回应了上述共情观点谈论中的问题2,即共情动因是知觉还是理性。从共情发生机制角度,可以用感情共情和认知共情涉及的大脑构造不同来阐明:现有神经影像学研究证明了镜像神经元系统自发性反应的存在,感情共情涉及的特异性脑区是额下回、前扣带回,认知共情涉及的是腹内侧前额叶[30]。这些神经系统相互浸染并部分重叠,并且都参与了终极的行为输出[31]。感情共情险些与生俱来,反应过程趋于自动化,认知共情则是基于知识和履历进行推理和理解,加工过程更加繁芜,更多地依赖前额叶等脑区的成熟[32]。
感情共情险些无所不包,乃至打哈欠传染、橡胶手错觉(Rubber Hand Illusion)征象都被纳入了感知-行动模型;认知共情紧张依赖自我报告,是难以衡量的。这给共情传播留下了很大的批评空间。只管生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对理性和直觉谁更强大各自为政,哲学家们对此也莫衷一是,但在考虑中不雅观问题时,在共情研究中区分感情和认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感情共情”观点无所不包的弊端,同时一个理性的认知共情观点,能够更好地在社会建构话语中发挥“共情”的积极力量,有利于进一步展开对共感情化和共情实践的磋商。
二、共情的浸染
共情传播之以是成为研究热点,不仅由于共情传播征象的广泛存在,也基于其传播效果和影响。
(一)共情具有宏不雅观社会道德意涵,也有微不雅观社会生活意义
对专业人士中的精神科年夜夫和生理学家而言,共情是其丈量、阐明和治疗的工具,缺少共情是自闭症等精神病理学的紧张症状之一[33]。对政治家而言,共情有助于亲社会行为,能够发展社会理解、坚持人际关系[34]。
对普通大众而言,“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等时常见诸社会生活道德说服。社会问题涌现的缘故原由每每会被归结为缺少共情,刻意为之地练习共情可以被用来勉励他人做出良善之举[35](P.87)。
大众既是共情工具也是共情者。社会各领域普遍将共情作为一种说服技能以达成各自目的:戏剧影视便是通过情绪操纵来争夺不雅观众,广告通过让受众与广告中的主人公共情进行商业说服,纵然是讲求客不雅观公道的新闻宣布也深谙通过叙事和影像来引发受众共情。例如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通过拍摄城市贫民生活,震荡了美国人的良知由此引发社会福利的改革,里斯也成为了20世纪初“扒粪运动”的先驱者。
(二)共情有积极效果,也有悲观效果
如果将共情在社会生活、政治和生理治疗中的道德说服浸染视作积极影响,与之相对,对“共情”的当心自20世纪30年代就已涌现:二战时德国剧作家们就意识到受众对舞台上演员的共情在政治上是危险的[36](P.15)。美国学者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在《电影和品行》一书中描写了电影是如何让不雅观众彻底地认同情节或主人公以至于阔别自身日常行为[37](P.30-50)。虽然布鲁默并未利用共情一词,但谈到电影让受众产生了恐怖、悲哀、眼泪和爱的感情且失落去自控能力,这与本日的盛行偶像文化所碰着的批评颇为类似。为理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学家、生理学家和教诲事情者环绕电影对儿童的情绪和态度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1934年,好莱坞《海斯守则》(Hays Code)颁布,在色情和暴力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7](P.196)。媒介暴力是个传统的话题,媒介上的暴力内容是否会引发受众模拟尚无定论。但共情研究的荟萃剖析显示,暴力媒体利用与儿童中期至成年初显期个体的感情共情和认知共情都有负干系,个中与感情共情的干系强于认知共情,被试的年事、智能媒体的利用均可调节暴力媒体利用与共情的关系[38]。打消揭橥偏倚,仅是考虑到可能涌现的负面影响,都值得内容创作者在暴力展示上更加慎重。
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是感情共情的紧张批评者之一,他认为在道德领域感情共情可能会产生好结果但也会导致不公正[35](P.28-29),该当先理性思考再谨慎共情。与乔纳森·海特的直觉引领道德判断的不雅观点类似②,布卢姆认为并非只有感情共情才能引发道德判断,宗教道德情绪也能导致道德判断,因此共情不能包治百病;此外,共情并不总是道德的,共情的道德标准可能与另一领域的道德相冲突[35](P.30-32)。例如在“舆论审判”“防卫过当”等话题中,受感情共情影响的受众的不雅观点态度可能与其他道德不雅观乃至法律相冲突;感情共情还具有焦点狭窄、被个人偏好旁边、聚焦于特定个体的缺陷[35](P.33-38)。后两种情形下,共情力量大于公正时会导致不公正。大眼睛女孩苏明娟《我要上学》的照片是希望工程的宣扬标志,照片揭橥后人们纷纭对穷苦儿童施以援手,对苏明娟定向捐助,随着家庭条件好转,苏明娟和家人把好心人的定向捐赠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39]。通过媒体聚焦引发受众共情使得社会资源汇聚于个人或名人身上,每每会引发不公正的批评,类似案例的还有有名运动员傅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旅游包车遭遇临时加价的乞助信息后,当地管理方当天晚上就发出了惩罚通报。网络舆论在肯定其惩罚速率和力度的同时也不禁置疑:如果乞助的不是傅某呢?这当然不是“共情”的错,但公正却是数字时期共情传播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共情定义中的问题3“情绪匹配”还提示我们,共情并不总是和被共情者怀有同种感情:环境成分的浸染会导致同背景情形下涌现不同共情反应乃至是反社会行为,即所谓的“幸灾乐祸”,或者对施害者共情。例如网络欺凌,当察看犹豫者对网络欺凌者产生共情、对其不雅观点认同以及受到从众生理影响时,随意马虎转变成网络欺凌者,从而引发网络欺凌的扩散[40]。
此外,还要考虑到对身处悲观情境中的他人共情会引起共情者的负脾气绪体验[41]。如新冠肺炎疫情下,过度的媒体参与并引发共情可能导致受众负面感情增加[42]。
总之,非理性共情、过度共情、共情偏差均会引发负面悲观后果。
三、共情的影响成分
现有研究支持共情存在认知和感情二元划分,存在积极和悲观的浸染,但对共情机制的研究还存在诸多磋商空间。本文在此做大略梳理,须要指出的是,由于对共情的定义和所利用丈量方法存在差异,研究方法过度依赖主不雅观/自我报告丈量,导致某些研究结果可能不一致。
(一)影响共情的个体成分
在阐明共情的个体差异时,遗传是紧张中介成分[43],年事、性别等影响个体共情发展。表不雅观遗传学方面,感情共情比认知共情具有更强的遗传根本,感情共情的遗传力高于认知共情③。荟萃剖析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镜像神经元系统在共情中可能发挥浸染的不雅观点[44]。脑电研究表明共情的感情和认知身分在韶光加工过程上存在分离,感情分享过程早于认知调节过程[45]。
1.年事:感情共情和认知共情有不同的发展轨迹。支持感情共情的大脑部分在婴儿期间就已经生动并发展完毕,而支持认知共情的区域则在从童年到成年的发展过程中更为持久[46]。因此,感情共情在全体发展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认知共情从幼儿期到青少年或成年早期稳步发展[47];进入成年中晚期后感情共情回升,认知共情有所低落[48]。研究创造,个体的共情准确性在青春期(14~17岁)不断增长,在成年早期(25~35岁)达到顶峰,在成年中期(45~55岁)开始低落,老年人的共情准确性低于年轻群体[49]。但在须要调用先验知识的共情方面,老年人的共情准确性并不亚于青年人[50]。老年人对积极感情与悲观感情共情不同,即老年人在感情共情中表现出积极倾向,对积极感情倾向增多,对悲观感情倾向减少[51]。
2.性别:共情随着年事变革在性别中开始涌现差异,一方面与个体自身的生理成熟有关,另一方面与社会性别角色方向有关。生理上,随着年事增长,催产素有助于感情共情,睾丸酮则与认知共情呈负干系。社会角色上,女性的性别角色以关注他人为导向,与共情有直接干系,而男性的性别角色以关注公正公道为导向,与共情没有干系,当两性习得各自的性别角色往后,性别共情表现就涌现了差异[52]。神经科学研究认为,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高的情绪反应能力,男性表现出更多的大脑区域来掌握认知同理心[53]。也有研究指出,实验范式存在性别差异但比较眇小,在自我报告丈量办法下,女性方向于将自己描述成更有同理心的人[54]。
(二)影响共情的环境成分
个体对他人情绪的感想熏染程度不同,可能源自家庭环境、政治、权力、种族、文化和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影响。
1.认知共情受环境关系影响。研究创造,环境成分对家庭成员共情的影响超越了遗传关系[55]。父母行为和亲子关系的质量是儿童共情发展的主要成分[56],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促进亲社会行为[57]。而差错关系(Peer Relationship)质量的中介调节乃至强于亲子关系[58]。
2.社会经济地位涉及个体在社会构造中的经济地位、教诲水平和职业等方面。一样平常认为,低社会地位组比高社会地位组更能准确地判断他人情绪,有更高的共情准确性,[59]高经济地位组的认知共情水平高于低经济地位组,在感情共情上相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能够感知到他人的个人痛楚水平越低[60]。但在其他研究中,这种效应可能被自我中央主义和利己主义等成分调节[61]。简言之,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影响一个人是否须要关注外界,越关注外界共情能力越高。
3.种族和社会群体身份对共情的影响表现为:对熟人共情的准确性显著高于对陌生人共情[62],对群体内与自己有相似经历和相似文化背景人群有更高共情反应和更多的帮助行为[63]。如白人大学生报告自己对白人被告有比黑人被告更强的共情绪,表现出对种族内部成员的共情倾向[64]。将来自汶川地震灾区和非灾区的中学生作为对照组,稽核他们对地震受灾民众的态度时创造:中国中学生帮助云南受灾民众的意愿显著高于帮助日本受灾民众的意愿,汶川地震灾区的中学生共情的程度和帮助云南受灾民众的意愿显著高于非灾区的中学生[65]。
4.跨文化共情。不同的文化背景通过影响共情双方对感情、思维的理解和态度,从而影响共情准确性。共情的道德判断上,西方文化倾向平平分派的共情,而中国文化更加强调对内群体成员的道德责任。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共情存在内群体偏差[63],有研究认为东方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共情能力更高[66],与东亚被试比较,英国被试报告了共情关注更高,共情准确性更低[67]。
我们很难将文化、种族、社会群体身份分割开来剖析其对共情的影响,这部分研究值得单独进行深入磋商以应对国际传播和跨文化共情实践。
四、共情传播理论根本:共情理论模型
通过对共情观点史、浸染的梳理可见,共情的传播历时长久且有诸多议题可拓展,特殊是在数字共通理念下,文化传播与共情、媒介暴力与共情、新兴数字传播技能与共情等问题都值得进行细致剖析,这不仅是针对当前数字化技能下贱传能动性的积极反思,也是“重构数字行动者的交往规范,培养和优化行动者网络的交往理性”[4]的有效手段。
现有聚焦共情影响成分的生理和神经科学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共情的形成机制和内在过程,为理解共情传播供应了有代价的理论框架。当前共情理论模型大致包括如下几类:一是从感知者角度可以分为感情共情和认知共情两类;二是从被共情者角度出发,紧张磋商被共情者的特点,以及表情、措辞等如何影响共情过程;三是共情发生机制角度,紧张包括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④和前述的感知-行动模型等。这些模型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共情的实质和发生机制,为实证研究供应了理论根本。
考虑到纵然是单一的共情过程,也必须至少将行为刺激、行为感知、共情共鸣和共情表达结合在一起[68]。本文将在以下两个主要理论根本上构建共情传播模型。
(一)共情准确性理论
虽然传播互换中误读不能完备避免,但从传播者尤其是组织传播角度看,误读应尽可能被避免[69]。准确共情有助于促进社会沟通,至少让人们有机会从感情共情进入到认知共情中去思考同样情境下对方的感想熏染。但上述研究创造阐明,要进行准确共情并非易事,不仅要考虑个人遗传特质成分,还有社会环境成分的繁芜影响。
为理解决共情丈量问题,生理学家威廉·伊克斯(William Ickes)等人提出了共情准确性(Empathy Accuracy)观点,将其定义为个体准确地理解和表达他人情感及生理状态的能力,强调应采取直接、实时的评估而非仅依赖自我报告,将“目标人的实际思想和感想熏染”与“感知者报告的相应的推断思想和感想熏染”进行比较[70]。
在衡量共情时,研究者强调区分共情理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共情表达(Empathic Expression)和共情沟通(Empathic Communication)三个关键共情过程[68]。当共情准确性被严格的理论术语定义时,仅指共情理解。但当为实证研究的目的定义共情准确性时,常日有必要扩展其定义,将共情表达包括进去,由于只有当感知者的共情理解以某种形式表达出来时,才能评估它的准确性。
共情理解指个体能够敏锐地洞察并深刻理解他人的感情体验和内心天下。这种理解不仅包括对他人当下感情状态的识别,还涵盖了对其情绪背后的深层缘故原由、动机以及个人经历的理解。共情理解哀求个体具备高度的情绪敏感性、感情识别能力以及对他民气情的换位思考,确保对他人情感的解读尽可能贴近其真实感想熏染。
共情表达是指个体能够恰当地将自己的共情理解以措辞或非措辞办法传达给被理解的工具,使其感想熏染到被理解和收受接管。有效的共情表达哀求个体利用符合对方情绪体验的措辞、语气和身体措辞,以确保情绪共鸣的准确通报。共情表达不仅有助于强化人际关系中的情绪连接,还能供应情绪支持。
共情沟通关注共情理解与共情表达在人际互动中的动态交互过程,强调对话性和辩证性。在这个过程中,共情理解通过双方的互换得以深化和发展,形成一种基于相互理解和收受接管的沟通模式。共情沟通哀求双方保持开放、诚挚和谛听的态度,通过持续的信息交流和反馈,不断调度和优化对对方情绪状态的理解,促进深层次的情绪共鸣和社会理解。
(二)共情循环理论
共情循环(Empathy Cycle)由罗杰斯的学生巴瑞特-伦纳德(Barrett-Lennard)提出,该模型由一个三阶段的共情循环往来来往组成,用于描述在直接人际交互中A(感知者)对B(目标工具)的共情相应过程[68]。
第一阶段是共情共振(Empathic Resonotion)。当B以某种办法表达个人情绪时,A产生对B感情的共鸣,即在内心深处对B的感想熏染进行相应和共振。
第二阶段是共情传达(Expressed Empathy)。A考试测验将自己的理解和共鸣传达给B,通过言语、行为或其他形式的沟通让B知晓自己正在共情地理解和收受接管他的情绪。
第三阶段是共情吸收/意识(Received Empathy)。B实际吸收到并意识到A传达的共情信息,即对A的共情表达有所觉察和确认。
此过程循环往来来往,三个阶段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即内在的共鸣、外在的沟通和对方的吸收可能存在不完备同步的情形。
共情循环模型强调了共情不仅是瞬间的情绪共鸣,更是一个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循环过程,每个阶段都是构造化的。受该模型启示,共情传播研究可以更风雅地从共情的各个层面,如共鸣、沟通和吸收的效果,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入手。
事实上,伊克斯的研究同样强调了反馈的主要性。他提到了共情的元知识(Metaknowledge)的缺失落可能导致共情者在判断他人情绪时涌现偏差,影响共情过程的准确性,这里的元知识即共情者对自己共情能力的认识不敷、缺少准确的自我评估,这可能源于他们很少寻求共情准确性的反馈,或者所收到的反馈不敷以让其理解自己在共情能力上的相对位置[70]。
(三)小结
共情准确性强调了传播过程中准确理解并表达的主要性,提示传播者需提升情绪敏感度、感情识别等认知共情能力,通过精准共情表达强化与受众间的情绪联结,增强内容的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共情循环理论则揭示了共情作为一种动态交互过程的内在机制,它由共情共振、共情传达与共情吸收三个连续且循环往来来往的阶段构成,提示传播者重视反馈,确保共情信息的准确传达与被感知。
五、基于大众传播实践的共情传播模型
共情准确性与共情循环理论为共情传播供应了主要的理论框架,强调了提升共情能力、实现认知共情与有效反馈在构建高质量共情传播中的浸染。论文综合“共情准确”和“共情循环”两个理论模型,结合传播行为特点,总结提出基于大众传播实践的共情传播模型(见图1)。该模型认为共情实践要明确主体客体、理解为何共情、节制如何共情,从而提高共情准确性,发挥共情的积极浸染,减少其负面浸染。
(一)明确共情传播的主客体:感知者与目标工具
由于自我-他人区分的失落败会导致自我中央偏见,将自己的感情或精神状态投射到他人身上,影响共情准确性,以是传播者要有“自我-他者”的意识,并能够将二者适当转化。
首先,传播者既是感知者(共情者),也是目标工具(被共情者),还会随详细情形转变主客体身份。传播者是事宜亲历方,传播其个人的经历、感想熏染、感情,传播者便是目标工具;传播者通过叙事、画面等转述通报第三方他者不可视的内部生理状态,传播者便是感知者。经由传播者“转译”后,感知者的目标工具既包括传播者,也包括作为故本家儿角的第三方。
其次,传播者不对所传播内容准确共情,不理解受众因何、如何共情,就不能将共情通报给受众。在传播模型中,如果传者认为传播内容无法通过评估,就不会进行下一步的共情表露;同样,进入共情表露阶段,传播者要谨慎处理共情传播实践,以免将个人感情或精神状态投射到他人身上,“添油加醋”造成内容不公道或不真实,影响共情准确性。
在共情传播特殊是国际传播过程中,以家国叙事和以个体视角来进行传播的效果可能有很大不同,这意味着传播者特殊是机构传播主体须要具有共情转译的能力,当“自我”比较宏不雅观时,不仅要思考传播内容是否以及如何能引发自身共情,也要考虑受众个体和文化社会语境下的共情成分。
(二)明确如何共情:理解并利用共情机制
生理学研究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实验多以二元互动(Dyadic Interaction)范式为主,即两人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往过程,但数字时期的共情传播由于参与主体和传播渠道的变革,显然须要超越这一范式,在共情的表达、沟通、理解上充分利用共情发生机制的干系研究创造。
共情过程中,被共情工具通过措辞、表情、动作等办法供应关于自己感想熏染与想法的线索,感知者吸收、加工这些信息,并基于此实现共情[71]。由于共情双方身处特定的社会环境,对社会信息的理解和加工会受到社会文化等成分影响。因此共情表露、共情传播和共情理解是动态交织的。
1.共情表露:意愿与能力
即目标工具的表露意愿和表露能力。作为目标工具的被共情者表现力越强、表达越准确,共情准确性更高。对个体而言,表露意愿更可控,但表露能力相对难以自我提升[71]。对有组织传播或机构媒体而言,把握主体的共情表露意愿、呈现捕捉其表露过程、引发其表露能力便是调动共情的关键。
2.共情传播:形式、渠道和内容掌握
在形式方面,从传播的技能倾向看,面对面的直接人际互换和对话更有利于共情传播。但在万物皆“云”上的时期,以媒体为介质的传播中,措辞和笔墨材料的共情准确性高于纯挚的视觉材料。个体在面对视觉信息(如表情、肢体措辞)时更易发生高水平的情绪共情,但这种高水平的共鸣可能不利于共情的准确性[71]。无论是推断想法还是感想熏染,听觉单通道对共情准确性的贡献都优于视觉单通道,视听双通道和听觉单通道对共情准确性的贡献依赖于推断任务本身。推断想法时,听觉单通道和视听双通道的准确性相称;推断感想熏染时,听觉单通道比视听双通道更准确。[72]
在渠道方面,由于方向于空间倾向的书面笔墨和当代电子媒介推动了知识的抽象化、标准化和快速扩散[73](P.83),以是媒介渠道可能降落对情境细节和个体差异的关注,转而聚焦于普遍规则、统计数据和抽象不雅观念。而过度抽象化可能导致个体在吸收信息时减少对他人主不雅观体验的深入理解和情绪共鸣,从而对共情传播构成寻衅。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网络环境中,信息的碎片化、匿名性和快速消费可能导致情绪共鸣和深度共情的减弱。实验证明新的传播技能对共情有一定的影响,但其浸染机制并不明确,也可能被浮夸了,例如:受众阅读电子版和纸质版的共情反应并无差异[74];VR传播能提高感情共情,但不能提高认知共情,VR在增加共情方面并不比笔墨材料更有效[75],其对共情的影响是通过用户认知来调节的[76]。
上述研究提示,只管目前已经全面进入视频时期,但互换仍是第一位的,充满细节的措辞和笔墨内容依然“为王”,视觉乃至虚拟现实体验是锦上添花但独木难支。例如要与盲人产生共情,让共情者戴上VR设备并不一定比直接蒙上眼睛好;阅读一段描述盲人遭遇生活中不便的笔墨,共情效果可能也不比戴上VR设备差。音乐或许对唤起情绪共鸣有帮助,但短视频中模板式的、与内容感情基调不符的配乐,可能会起反浸染,而与内容相契合的配乐则可能提高共情准确性。简言之,技能在共情中不是决定成分,数字化是人类面临的客不雅观环境,而不是共情传播的办理方案。
在内容方面,共情传播中“内容为王”的标准仍旧有效,但须要深层理解和细化。由于共情受人际关系调节,互动叙事可以增强共情,不雅观点说服比内容呈现更能够引发共情[77],因此内容的定位、情绪触发和干系性仍旧在共情传播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提示传播者:一是要看重互动元素的融入,强调建立包括人际关系、社会联系等在内的连接,探求共性;二是要确保内容的质量、深度和干系性,以供应更有代价的共情体验,并关注群体内外差异,理解和认可群体身份对共情的影响,确保内容能够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产生共鸣;三是明确表达不雅观点、态度、情绪,以便不雅观众更好地理解和共鸣,从而提高共情传播效果。
3.共情理解:机制与原则
共情理解即感知者的信息吸收意愿和能力。共情理解影响成分提示,共情实践不能被理解,既有生理“不能”,也有生理“不能”。共情者的信息加工能力受年事、性别、身体机制等影响,在客不雅观上影响共情理解。1749年,狄德罗在《论盲人书简》中指出,受感知能力限定,盲人的共情能力是残缺的,常日会让人遐想到疼痛和同情的所有符号中,他只对悲鸣有反应[78](P.30)。普通来说,人们无法感知自己从未感知过的他人情绪。而个体的视角选择、认知风格⑥、情商和心智能力等则在主不雅观上影响其对共情信息的吸收理解。
共情理解同时提示:共情实践既须要共性,也需差异化。
共性是基于全人类共通的或某类人群共通的情绪实践共情传播。感知者与目标工具的社会关系与互动历史对共情理解有显著影响,由于长期相处人群之间建立了共享的认知框架,积累了关于对方感情表达模式的知识,每每能更准确地理解彼此的感情。但大众传播中,很难哀求双方具有完备相同的社会关系和互动历史,因此可以以传播工具群体共性为切入点,例如:对老年人群体,应该更侧重供应积极的认知共情内容,强调正面的情绪体验和建立情绪连接;考虑到老年人群体常日具有丰富的先验知识和履历,可以通过在共情传播中融入其熟习的语境和情境来匆匆进共情连接。而对人群的垂直划分,目前已经可以通过基于用户兴趣、代价不雅观和感情方向构建的用户画像来实现,并通过算法推送与其共情能力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内容。
差异是基于特定的社会情境。特定的情境成分(如压力水平、韶光压力、环境滋扰等)可能影响个体对他人情绪的专注度和理解准确性。例如,在高压或混乱的情境中,个体可能更难专注于他人的感情,导致共情水平低落。因此在考虑传播渠道时,社交媒体、流媒体视频平分歧平台,乃至新闻媒体、娱乐内容供应商平分歧主体的传播策略应有所差异。
总之,要寓“情”于不同种别内容,选择不同传播渠道提升共情传播效果。
(三)明确为何共情:共情与交往理性
前述研究表明,共情不仅会带来积极的亲社会效果,也可能会给共情者带来悲观的影响,还要当心受众对施害者共情。数字共通理念下,在感情共情上产生准确的认知共情,才能实现理性社会建构。因此,共情传播实践必须要考虑为何共情——是追求短期的感情共情,还是追求稳定的认知共情;是在繁芜的多元传播互动中为受众供应自由的共情工具,还是贯注灌注主不雅观的、由传者主导的感情感想熏染。在海量的数字化感情材料中,如何才能发挥认知共情的浸染,提高受众的认知共情能力,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新闻领域、文化教诲领域等都不尽相同。
追求短期的感情共情,旁边受众感情,可能会引发群体极化,造成整体范围上的不公正。比如“后原形”时期的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等极化征象,都是由片面事实或虚假信息大范围传播的感情唤起。
追求稳定的认知共情,须要建立在传受双方平等互换、相互而非单方面理解的根本上进行。文化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生理构造,而且从现有研究丈量手段看,认知共情传播短期内可能很丢脸到即时的社会认知效果改变。因此在跨文化和国际传播过程中,有必要防止“自我共情”“自我冲动”,而应追求长期稳定的认知共情和认同。建立在对话与互助中的理解,才能超越文化倾向,超越把他者文化当作知识理解与兴趣知足的局限,形成建构跨文化传播关系的可能性[79]。
此外,还要意识到共情并不一定意味着行动。人们通过大众传播可能会对他人的苦难共情,但并不虞味着会施以援手。共情的利他行为存在性别、社会阶层等中介调节成分。同时共情具有神经调节机制,过度共情刺激会造成共情疲倦[80]。以调动利他行为为目的的共情传播,有必要在传播内容、形式、渠道、刺激程度、频次等方面做出适当调度。
(四)供应共情的社会支持与反馈
来自他人的支持与反馈有助于个体调度和验证其对他人情绪的理解。确认共情理解精确的积极反馈会增强个体信心和能力,反之可能阻碍共情效果。在传播实践中,设置共情反馈机制成为现实问题。特殊是当前传播高度依赖平台的情形下,反馈机制的建立就显得更为急迫。
现有传播实践中,对互动反馈的风雅化运作做得远远不足,不仅让人印象深刻的系列宣布传播很少得见,日常的根本评论反馈互动也不会将共情作为侧重点。随着人工智能大措辞模型的发展,利用AI进行赞助剖析或成为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技能剖析用户在平台上的行为数据(如浏览记录、互动行为等),供应个性化的共情理解评估报告;利用AI对潜在的共情盲点或过度共情方向进行剖析和建议,通过人机互动办法向受众直接反馈。
六、结语:共情传播的术与道
共情传播既是术也是道:它是技巧,由于共情有助于推动社会互换,为社会议题和道德评价供应了一个交汇的平台。只管这种情绪共鸣中可能存在非理性成分,但在消费文化的环境中,由于个人、机构乃至国家在名誉、利益和权力方面的追求,情绪在各种传播形式中无法完备肃清。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该当在原则层面上准确理解共情,深刻理解共情的正面和负面效应,节制共情的感情和认知机制,明确共情的目的所在。
共情传播的研究领域正在迅速发展,基于上述对共情观点史的回顾和及其在传播中的谈论,本文认为,共情传播模型能够有效厘清共情传播的主体性和功能性问题,确保未来研究的同等性。以该模型辅导的共情实践能够使得交往理性和大众感情在碰撞中交汇,在共情传播过程中增强"大众同理心(只管可能是难以丈量的),实现共情传播的正效应,避免由道德不雅观念和关系亲疏等带来的偏见共情。
须要指出的是,本文侧重有组织传播中的共情议题,且因此“共通”这一效果为目标论述的,对付自传播和商业传播中“共情”的征象机制和效果批评涉及不多,这是由于本文认为,将以社会建构为目的的议题和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议题分离开来进行剖析,能更好地在一定篇幅内说清问题。
从2022年末全新对话式AI模型ChatGPT正式发布,到2024年开年的笔墨天生视频模型Sora,人工智能进展之快让社会科学为之瞩目。未来的传播领域,人工智能将发挥到何种程度让人充满想象,不同于与人共情,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将面对的是可打算共情和人与人工智能共情。这将寻衅现有共情研究理论,也须要大量的神经科学、打算机人工智能的不雅观察实践和知识创造。反之,人工智能是否终有一天会与人类共情,识别人类心智?人类在个中的浸染是什么?主体性何如?都有待进一步探索。
注释:
①运动移情可以定义为在不雅观察他人期间对富有表现力的肢体措辞的自动模拟和同步,如打哈欠动作的传染。
②乔纳森·海特认为,道德判断紧张由直觉引起,理性随后为之辩解,而不是先有理性才做出道德判断。拜会:[美]乔纳森·海特《象与骑象人》,杭州:浙江公民出版社,2012年,28-29页。
③干系研究参阅Abramson L, Uzefovsky F, Toccaceli V,et al.“The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origins of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mpathy: Review and meta-analyses of twin studies”.In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No.114,2020;Melchers M , Montag C, Reuter M,et al.“How heritable is empathy?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measurement and subcomponents”.I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No.5, 2016;颜志强、苏彦捷《认知共情和感情共情的发展差异:元剖析初探》,《心理发展与教诲》,2021年第1期。
④心智能力指个体的思维办法(如直觉型与剖析型)、认知灵巧性以及理解他民气理状态(如信念、希望、意图)的能力。
⑤本模型图由作者整理绘制。解释:a模型角色中,括号外为紧张角色,括号内为次要角色,例如在自传播中,目标工具既是被共情者也是传者,但紧张是被共情者;b第二栏与第四栏框线中的共情沟通机制同时发生,各有侧重,在传者视角紧张强调感情和认知共情绪受的转译,在受者视角紧张强调共情传播的影响成分如何影响共情准确性;c虚线内经历反馈循环后的第二轮共情传播并不一定会发生。
⑥认知风格描述的是个体感知、组织和对刺激的反应办法,是“形式”或“过程”,而不是认知的“内容”或“水平”,干系研究拜会:Decety J,William Ickes(eds.).The Social Neuroscience of Empathy.Cambridge,MA:MIT Press,2011,p36.
参考文献:
[1][美]韩瑞(Eric Hayot).假想的“满大人”:同情、当代性与中国疼痛[M].袁剑,译.南京:江苏公民出版社,2013.
[2][美]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期间公众年夜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M].陈湘静.译.南京:江苏公民出版社,2011.
[3]中国知网共情传播学术关注度指数[EB/OL].(2024-02-03)[2024-02-03].https://kns.cnki.net/kns/search?dbcode=CIDX&kw=%E5%85%B1%E6%83%85%E4%BC%A0%E6%92%AD.
[4]吴飞,傅正科.“数字共通”:理解数字时期社会交往的新假设[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6).
[5]胡翼青.我们该如何理解“数字共通”:基于媒介哲学的批驳[J].当代出版,2024(2).
[6]钟新,蒋贤成,王雅墨.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共情传播: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策略及效果剖析[J].新闻与写作,2022(5).
[7]Lanzoni S.Empathy: A history[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8]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9]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等.汉语外来词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10]李泽厚.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1]魏磊.感情体验是道德行为发生的契机[J].海内哲学动态,1986(8).
[12]谢静.移情与新闻采写[J].新闻大学,1995(2).
[13]Decety J, Yang C Y, Cheng Y.Physicians down-regulate their pain empathy response: An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study[J].Neuroimage, 2010(4).
[14]Wicker B, Keysers C, Plailly J,et al.Both of us disgusted in My insula: the common neural basis of seeing and feeling disgust.[J].Neuron, 2003(3).
[15]De G B, Snyder J, Greve D ,et al.Fear fosters flight: A mechanism for fear contagion when perceiving emotion expressed by a whole body[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4(47).
[16]Vitaglione G D, Barnett M A .Assessing a New Dimension of Empathy: Empathic Anger as a Predictor of Helping and Punishing Desires[J].Motivation & Emotion, 2003(4).
[17]Pittelkow M, aan het Rot M, Seidel LJ, et al.Social Anxiety and Empath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21 (1).
[18]Jabbi M, Swart M, Keysers C .Empathy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the gustatory cortex[J].Neuroimage, 2007(4).
[19]Krach S, Cohrs J C, de Echeverría Loebell N C, et al. Your flaws are my pain: Linking empathy to vicarious embarrassment[J]. PloS one, 2011(4).
[20]Harrison N A, Tania S, Pia R ,et al.Pupillary contagion: central mechanisms engaged in sadness processing[J].Social Cognitive &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06(1).
[21]陈晶,史占彪,张建新.共情观点的演化[J].中国临床生理学杂志,2007(6).
[22]Carlo G, Edwards CP (eds.). Moral motivation through the life span[M]. Lincoln:U of Nebraska Press,2005.
[23]Preston SD, De Waal FB. Empathy: Its ultimate and proximate bases[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002(1).
[24]Goldie, Peter, Amy Coplan(eds.). Empathy: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5]Maibom H. L. (ed.). Empathy and morality[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26] [美]马丁·L·霍夫曼.移情与道德发展:关爱和公道的内涵[M].杨韶刚,万明.译.哈尔滨:黑龙江公民出版社,2003.
[27]Shamay-Tsoory S G.The Neural Bases for Empathy[J].The Neuroscientist, 2011(1).
[28]Cuff BMP, Brown SJ, Taylor L,et al. Empathy: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Emotion Review,2016(2).
[29]Duck S, Hay D F, Hobfoll S E ,et al.(eds.).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ory,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s[M]. Oxford: John Wiley & Sons,1988.
[30]Decety J.The Neurodevelopment of Empathy in Humans[J].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2010(4).
[31]Zaki J, Ochsner K.The neuroscience of empathy: progress, pitfalls and promise[J].Nature Neuroscience, 2012(5).
[32]颜志强,苏彦捷.认知共情和感情共情的发展差异:元剖析初探[J].心理发展与教诲,2021(1).
[33]Blair R J R.Responding to the emotions of others: dissociating forms of empathy through the study of typical and psychiatric populations.[J].Conscious Cogn, 2005(4).
[34]Eisenberg N, Fabes RA. Empathy: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 to prosocial behavior[J]. Motivation and emotion,1990(2).
[35][加] 保罗·布卢姆.摆脱共情[M].徐卓,译.杭州:浙江公民出版社,2019.
[36]Bertolt B. Indirect Impact of the Epic Theatre (Extracts from the Notes to Die Mutter)[M]//Lanzoni S. Empathy: A histo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37]Blumer H. Movies and Conduct[M]. New York: Macmillan & Company ,1933.
[38]刘富丽,苏彦捷.暴力媒体利用与儿童青少年共情关系的元剖析[J].生理技能与运用,2017(10).
[39]让爱与希望生生不息[N].公民日报外洋版,2023-01-12.
[40]竭婧,林雪婧.网络欺凌的产生、扩散和消退机制[J].社区生理学研究,2022(2).
[41]郭晓栋,郑泓,阮盾,等.认知和情绪共情与负脾气绪:感情调节的浸染机制[J].生理学报,2023(6).
[42]Chen X, Liu T, Li P,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Involvement and Death Anxiety of Self-Quarantined People in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The Mediating Roles of Empathy and Sympathy[J].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2020(3).
[43]Ebstein R P, Israel S, Chew S H,et al.Genetics of human social behavior[J].Neuron, 2010(6).
[44]Bekkali S, Youssef G J, Donaldson P H, et al. Is the putative mirror neuron system associated with empath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Neuropsychology review, 2021(1).
[45]Fan Y, Han S.Temporal dynamic of neural mechanisms involved in empathy for pain: An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study[J].Neuropsychologia, 2008(1).
[46]Tousignant, Béatrice,Eugène,et al.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the neural bases of human empathy[J].Infant Behavior & Development, 2016.
[47]Roth-Hanania R, Davidov M, Zahn-Waxler C .Empathy development from 8 to 16 months: early signs of concern for others[J].Infant Behavior & Development, 2011(3).
[48]王启忱,刘赞,苏彦捷.共情的毕生发展及其神经根本[J].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21(6).
[49]Wieck C, Kunzmann U.Age Differences in Empathy: Multidirectional and Context-Dependent[J].Psychol Aging, 2015(2).
[50]Rauers A, Blanke E, Riediger M.Everyday empathic accuracy in younger and older couples: do you need to see your partner to know his or her feelings?[J].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11).
[51]庞芳芳,陈玮,苏英,等.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共情差异——积极与悲观感情的分离[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1).
[52]陈武英,卢家楣,刘连启,等.共情的性别差异[J].生理科学进展,2014(9).
[53]Christov-Moore L, Simpson E A,Coudé, Gino,et al.Empathy: Gender effects in brain and behavior[J].Neurosci Biobehav Rev, 2014(46).
[54]Baez S, Flichtentrei D, Prats M, et al. Men, women……who care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n sex differences and gender roles in empathy and moral cognition[J]. PloS one, 2017(6).
[55]Abramson L, Uzefovsky F, Toccaceli V,et al.The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origins of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mpathy: Review and meta-analyses of twin studies[J].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20.
[56]Hana,Yoo,Xin,et al.Adolescents'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e Family Context: A Longitudinal Study[J].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3.
[57]Farrant B M, Devine T A J, Maybery M T, et al. Empathy, perspective taking and prosocial behaviour: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ing practices[J].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2012(2).
[58]Boele S, Graaff J V D, Wied M D ,et al.Linking Parent-Child and Peer Relationship Quality to Empathy in Adolescence: A Multilevel Meta-Analysis[J].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9(6).
[59]Kraus M W, Cote S, Keltner D.Social class, contextualism, and empathic accuracy[J].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11).
[60]郑颖. 社会经济地位对认知共情、感情共情的影响[D].河南大学,2022.
[61]Schmid Mast M, Jonas K, Hall J A.Give a person power and he or she will show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the phenomenon and its why and whe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2009(5).
[62]Thomas G, Fletcher G J O.Mind-Reading Accuracy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ssessing the Roles of the Relationship, the Target, and the Judg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3(6).
[63]陈梓轩,李雨悦,杨雨洁,等.谢绝还是收受接管共情偏好?公正共情道德认知的文化差异[J].生理技能与运用,2023(10).
[64]Johnson J D, Simmons C H, Jordav A,et al.Rodney King and O. J. Revisited: The Impact of Race and Defendant Empathy Induction on Judicial Decisions[J].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0(6).
[65]谭树华,王芳,许燕,等.3.11日今年夜地震后中国中学生共情与助人关系的研究:文化打仗的调节浸染[J].中国分外教诲,2011(11).
[66]Wu S, Keysar B.The Effect of Culture on Perspective Taking[J].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7).
[67]Atkins D, Uskul A K, Cooper N R.Culture Shapes Empathic Responses to Physical and Social Pain[J].Emotion, 2016(5).
[68]Barrett-Lennard GT. The empathy cycle: Refinement of a nuclear concept[J].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1981(2).
[69]Lau B K Y, Geipel J, Wu Y, et al. The extreme illusion of understanding[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22(11).
[70]Ickes W. Empathic accurac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1993(4).
[71]潘晗希,郭杨,高齐,等.共情准确性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J].运用生理学,2022(3).
[72]孙炳海,岳腾宇,李伟健,等.耳听为“实”,眼见为“虚”:推断任务对共情准确性视听通道效应的影响[J].生理科学,2023(2).
[73]Innis Harold A.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M].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74]Lene B S. Abbreviated Study Summary: Social cognition and empathic response to digital versus print media[EB/OL].(2015-07-06)[2024-02-29].https://archives.cjr.org/analysis/abbreviated_study_summary_social_cognition_and_empathic_response_to_digital_versus_print_media.php.
[75]Martingano A J, Hererra F, Konrath S. Virtual reality improves emotional but not cognitive empathy: A meta-analysis[J]. Technology, Mind, and Behavior, 2021.
[76]Shin D.Empathy and embodied experience in virtual environment: To what extent can virtual reality stimulate empathy and embodied experience?[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8(78).
[77]Barbot B, Kaufman JC. What makes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the ultimate empathy machine? Discern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change[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20(111).
[78][德]汉宁·里德.无处安顿的同情[M].周雨霏,译.广州:广东公民出版社, 2020.
[79]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
[80]Gainsburg I, Lee Cunningham J. Compassion Fatigue as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Believing Compassion Is Limited Increases Fatigue and Decreases Compassion[J]. Psychological Science,2023(11).
本文转自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