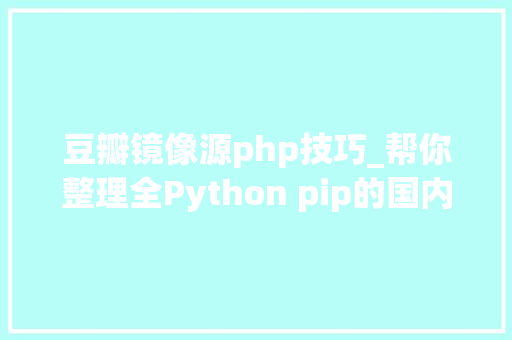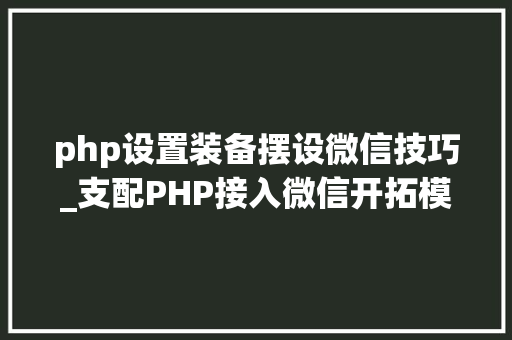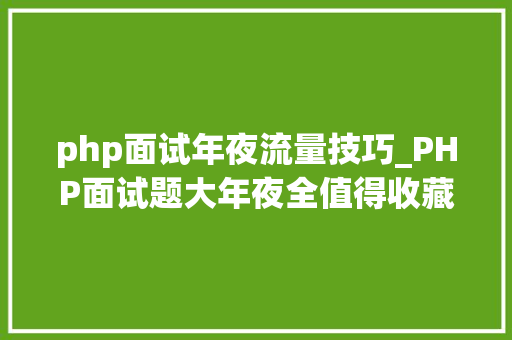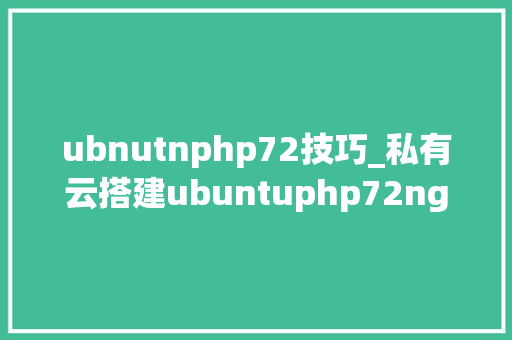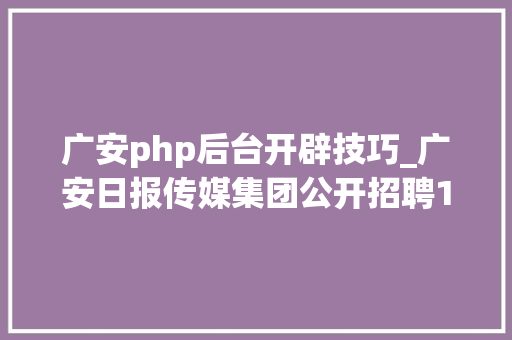《厚父》是清华简第五辑中的一篇,由于措辞古奥与《尚书》周初八诰近同,且篇中内容又涉时王与夏人后裔厚父的对话,公布以来备受学者重视。对付此篇的性子,学者间有“夏书”“商书”“周书”等多种不同说法[2]。我们认为此篇为“周书”,本文拟通过“卿事”一词源流的校勘对此作进一步论证,并就与《厚父》有关的周人经典重修问题谈谈我们的意见。
一、晚近简帛文献中的“卿士”与“卿士”考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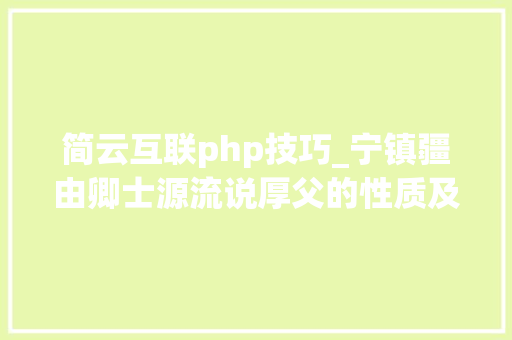
传世文献中,“卿士”是周王朝高等别职官,地位尊隆。故意思的是,“卿士”西周金文中一律作“卿事”,从无例外,这是学者们熟习的。晚近简帛文献中“卿士”要么如金文般作“卿事”,要么个中的“事”就作其他字形,总之仍旧不是如传世文献般作“卿士”。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刻意的区分?早期“卿事”的本义如何?它是如何演化为“卿士”的?这些问题古人或偶有关注,但并不系统,本文拟对此作一全面的梳理。
简帛文献中较早涌现“卿士”一词是郭店及上博简《缁衣》所引《祭公》。今本《礼记·缁衣》篇有引所谓“叶公之顾命”(“叶”当为“祭”之误)的话,个中云“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明有“卿士”,但郭店简、上博简《缁衣》篇对应的话,郭店简作“毋以嬖士息大夫、卿事”[3],上博简作“毋以嬖士疾大夫向使”[4],可以看出,对应今本“卿士”,郭店作“卿事”,上博简作“向使”,均与今天职歧。但请把稳,前面的“嬖士”用“士”,两种文献却与今本同等。由于有今本参照,郭店简的整理者直接在“事”后括注“士”。上博简“向使”之“向”与“鄉”读音附近,而“鄉”与“卿”古本一字;个中的“使”与“事”也是分解字的关系,就像金文中早期“卿事”每每写作“卿” [5],个中的“”从“史”,实在与“事”也是分解字的关系,以是上博简“向使”无疑也该当释为“卿事”。也便是说,在前有“嬖士”之“士”对照的情形下,上博简的“使”仍旧没有与“士”轻易趋同。
《缁衣》篇所引为《逸周书·祭公》,此后清华简此篇公布,对应文句作“毋以俾(嬖)士息大夫卿”,整理者直接将“”括注为“士”。与《祭公》篇同辑公布的《系年》篇又有“卿、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与《祭公》篇同形,整理者说即“李”字,并谓“李”与“士”读音附近,显然因此今本的“卿士”作标尺。但也有学者指出,鉴于郭店、上博、清华简前文都有“嬖士”,而后文却或作“卿事”,或作“向使”,或作“卿”,总之便是没有直接写成“卿士”,参考金文中的“卿事”,因此认为“卿”之“”以括注为“事”为妥当[6],我们认为是精确的。稍后公布的清华简《厚父》篇有文“命咎繇下为之卿事”,“卿事”与西周金文同,个中之“事”同样未写作“士”。这一来解释学者的谨严处理颇有道理,二来也暗示郭店、上博、清华简所引(见)《祭公》在前有“嬖士”的情形下,后面的“卿事”“向使”“卿”却始终没有径作“卿士”,并不是有时的。
由清华简“卿事”写作“卿李”,又要提到更早公布的包山楚简“阴侯之庆李”以及北大汉简《堪舆》之“庆李”,俱有“庆李”,学者受清华简启示认为“庆李”即“卿事”,“庆”乃“卿”之假借[7],可信。我们还可以为此说补充一条传世文献的证据。《礼记·祭统》载卫孔悝之鼎铭文云:“乃考文叔,兴旧耆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个中的“庆士”,古人即已指出当读作“卿士”[8],这解释“卿士”之“卿”确有假作“庆”者。其余,由清华简“卿李”假“李”为“事”,学者还联系提到传世文献的“行李”一词,并指出“行李”本指“人”(《左传》“行李”“行理”都有: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昭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9],其说是。故意思的是,出土文献也有“行李”,清华简《越公其事》第60简云:“焉始絶吴之行”,个中的“行”显然便是“行李”,整理者指出“行李”即“使人”。[10]网友“海天游踪”认为“行李”可读为“行使”,行人、使人也。“李”是“使”的假借单,且引清华简《系年》简137“王命平夜悼武君李(使)人于齐陈淏求师”即为例。[11]子居以为“行人”是标准称谓,“行李”“行理”“行使”皆为晚出。[12]既然“卿李”是“卿事”之假借,则“行李”之“李”恐也是“事”之借单,即指人的“行李”本当作“行事”。这方面的有力证据是,比来荆州考古事情者又公布了发掘品枣纸简《吴王夫差起师伐越》,此与清华简《越公其事》内容基本相同,个中《越公其事》的“行”,枣纸简作“行(使)”,对应“”的字作“(使)”,就像前举上博简《缁衣》“卿事”作“向使”,此处“行(使)”恐亦当是“行事”之借。由于早期文献中“事”与“士”常相通用,且“卿事”传世文献俱作“卿士”,笔者以为这种近乎青鸟使的“行李”或“行使”,都当读为“行士”,指往来、奔忙之“士”[13]。由于早期文献中“人”与“士”俱可作为笼统的他称,乃至合并称“人士”(《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这恐怕也是文献中他们又多被称“行人”的缘故:“行士”与“行人”,“人”与“士”的语法位置相称,故常可互换[14]。“行士”与“行人”都当是对那些出行、往来“人士”的称呼,而且同样有他称意味。
由上可见,传世文献“卿士”在简帛文献中以写作“卿事”为常,或者“事”假借为“李”或“使”,总之,便是没有径写作传世文献的“卿士”。尤其是清华简《祭公》及郭店、上博简《缁衣》所引以“嬖士”与“卿事(李)”对举,在两者相距如此之近的情形下,“卿事(李)”仍旧没有率尔趋同为“卿士”。为什么会有这种刻意的区分?我们认为这要从“卿事”的词源上才能找答案。
此前学者考镜“卿士”一职的源头,大多追溯到甲骨卜辞,如罗振玉、王国维均指卜辞即有“卿士”[15]。郭沫若也赞许罗氏的见地,而且认为《合集》37468“其令鄉史(事)”犹《大雅·常武》的“赫赫明明,王命卿士”[16]。后来唐兰、李学勤都肯定上述卜辞即最早的“卿士”[17]。但姚孝遂对此持否定见地,其读卜辞“鄉史于[]北宗”(《合集》38231)为“饗使于[]北宗也”,也便是将“鄉(饗)使”理解为动宾构造,即“宴饗”“使”的意思。姚氏遂谓罗振玉说卜辞有“卿事”之官,实为误解[18]。
实在,卜辞“鄉史(事)”这样的构造,除了罗振玉所举外,还有:“其执/弜执,呼归,克鄉王事。引[吉]”(《合集》27796)
学者已经指出此条之“鄉”与《合集》37468之“鄉”用法相同[19],但是《合集》27796“克鄉王事”实在不过是 “鄉史(事)”的繁构。也便是说,卜辞“鄉史(事)”也应与《合集》27796“克鄉王事”合并理解。在更多辞例参照的情形下,可知像姚孝遂那样读“鄉史(事)”为“饗使”也是有问题的。由于无论是“克鄉王事”,还是“其令鄉史(事)”,个中的“克鄉”“其令”如斯者,都意指某人可以承担或堪任某事,语较严明,如果仅仅是“饗”某人,语境似有不合。黄天树师长西席认为“鄉”用为“向”,理解为面向、趋向,因此将《合集》27796“弜执,呼归,克鄉王事”翻译为“不要执捕而呼令其归来,能为王事尽力”[20],虽然“趋向”“王事”这样的搭配较为可怪,但将“克鄉王事”理解为“能为王事尽力”则是大致准确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像卜辞“鄉史(事)”这样的构造中,“‘鄉’该当是行、做一类意义的动词”[21],这是很精确的见地。这样看来,“鄉史(事)”构造中,“事”以本字读即可,也便是当“事情”来讲,不必读为“使”。那么“鄉”字到底该作何读呢?“鄉事”与后来作为职官的“卿事(士)”是否有关联呢?
考虑到“‘卿’该当是行、做一类意义的动词”,而“趋向”“王事”之说又于文献无征,我们认为“卿”不当理解为“向”,而当读为“享”。“鄉”与“享”义近,金文中“用鄉”有时又作“用享”。但“享”当理解为“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诸侯服享”,“服”与“享”即同义复指。因此,卜辞“鄉事”即“享事”,而“享事”便是“服事”的意思。伯或父鼎(《铭续》231)有铭文:“宗人其用朝夕享事于嫡宗室”,即为“享事”的搭配,所谓“享事”于宗庙,实在即“服事”于宗庙也。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别的冲人,服在清庙”,于宗庙之中,正用“服”字。《周颂·清庙》“骏奔忙在庙”,即“奔忙”“服事”于宗庙。其余,“享”可训“服”,金文及早期文献中屡见其例。如克罍、克盉“享于乃辟”[22],即“服”于“乃辟”也。《尚书·洛诰》“汝其敬识百辟享”,孔传:“奉上之谓享”,所谓“奉上”即“服事”也。逑钟有“享辟先王”,“享辟”也是同义词连用,指服事、辟事先王。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无侮享君”,“享君”即“服君”也。其又云:“恒称其有若,曰享会余一人”,学者已经指出,“享”“会”系同义复指,乃服事、辅佐的意思[23],是很精确的。将卜辞“鄉(享)事”理解为“服事”或履职还有更靠近的辞例为证。周初大盂鼎铭(集成2837):“(王曰)今余唯命汝盂……敏朝夕入谏,享奔忙”。所谓“享奔忙”,即“鄉奔忙”,也便是“服奔忙”之职事。《尚书·酒诰》“奔忙事厥考厥长”,召圜(集成10360)铭文的“奔忙事皇辟君”,均“奔忙”与“事”连言,但是“奔忙”即“事”也。不唯辞例靠近,它们所处的措辞环境也近似。大盂鼎:“命汝盂……享奔忙”,与卜辞“其令鄉史(事)”,“享”“鄉”通用,又同为“令(命)”语义下的祈使语气,实在都是指令臣子服某职事。实际上,后来已明显职官化的“卿事”还保留这样的特点。如作册令方彝(集成9901):“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大雅·常武》:“王命卿士”。这些王命“卿事(士)”的例子,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王命鄉(享)事、服事或谓履职。再如《尚书·多方》:“多士……尔亦则惟不克享”,“不克享”与卜辞“克鄉王事”构词办法非常靠近,均强调“享(鄕)”能否“克”即承担的问题。《逸周书·商誓》又云“成汤克辟上帝”,参考前举逑钟“享辟先王”,“享辟”同义词连用,则“辟”也当是“服事”的意思,但是“克辟”实与“克鄉”近同,都是强调能够承担服事之职。
如将卜辞“鄉”理解为“服”,代入上述卜辞,可以说都文从句顺。《合集》38231“鄉事于[]北宗”,指“服事”或“履职”于“[]北宗”。《合集》37468“其令鄉事”,便是令某人服事、履职的意思,而《合集》27796“弜执,呼归,克鄉王事”的意思则是说:不要执捕,让他们归附,以服王事。总之,我们认为上述卜辞的“鄉事”构造该当读为“享事”,理解为“服事”、履职。卜辞“克鄉王事”,是希望某人能够承担王事,“其令鄕史(事)”,则因此祈使的语气命臣子服其职事。进而论之,我们认为卜辞“享事”或“服事”这样的动宾构造,正是“鄉事”后来职官化变为成词“卿事”的语义本源,由于臣子都有为“王事”“服享”的基本责任。换言之,“卿事”便是指那些“鄉(享)事”或“服事”的臣子。虽然罗振玉将上述动宾构造的“鄉事”径指为职官“卿事”有欠严谨,但就指出“鄉事”与文献中职官“卿士”的关联看,倒是不错的。当然,我们不要以为商代“卿事”只有“鄉事”这样动宾构造的散文式表达,由于商代晚期小子簋(集成 3904)云:“乙未,卿事赐小子贝二百”,此“卿事”指职官,明显已经成词化了,与西周金文习见的“卿事”完备同等。解释只管卜辞中尚有散文式的“鄉事”一词,但商代作为成词和职官化的“卿事”与散文化的“鄉事”是“共时”存在的。实际上,我们从大盂鼎“享奔忙”来看,“奔忙”貌似详细的动作词,但由上述《酒诰》、召卣中的“奔忙事”辞例来看,“享奔忙”实在也明显有职官的特色。
由散文化的“鄉事”到职官义的“卿事”,可知“卿事”之“事”紧张指事情之“事”,并非指“人”,而“士”最初便是指“人”的,并没有“事情”的意思。从文献及金文来看,指“人”的“士”乃至还可以作为男子之通称,《小雅·甫田》“以穀我士女”,所谓“士女”即“男女”也。《大雅·既醉》云:“其仆维何?厘尔女士”,此“女士”与《甫田》“士女”不过颠倒为文。高亨师长西席解为“女男”,谓“男女仆众”,吴闓生同之[24],良是。西周凤雏卜甲H11:1“王其巶祝成唐,肆御报士女”讲到献祭先人的人牲为“士女”[25],師㝨簋(集成4313、4314 西周晚)中记载周王室讨伐淮夷的俘获有“士女牛羊”,亦涉“士女”,他们的意思均应与《甫田》“士女”同,理解为“男女”。如此,则指“人”的“士”作为男子之通称可谓至为显豁。总之,从最基本的意义上看,“士”始终是指人的。不过,正如我们熟知的文献中“卿士”金文中多作“卿事”,实在从很早的时候起,单称的“事”也常可借指“人”。如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陟降其事”,《周颂·敬之》对应句子作“陟降其士”,学者早已指出“事”当指“人”。麦盉(《集成》9451)有铭文“厥事麦”,辞例与叔虞方鼎“厥士唐叔虞”同等,麦盉的“事”显然也是借为指人的“士”。农卣(《集成》05424)有“小大事(集成5424)”,训匜(《集成》10285)有“小大史(集成10285)”,个中的“小大事(史)”,都该当读为“小大士”,指大小官员。“事”可借为“士”,从训诂上也可以看出点痕迹。《说文》云:“士,事也”,这实在本于毛诗对“士”的训诂,如《小雅·祈父》“予王之爪士”、《桓》“保有厥士”,个中的“士”,毛传俱解:“士,事也”。作为王臣的“士”,又自有其所“事”之职守,也便是说,他们都是为君王做事、办事的。《假乐》郑笺即云:“卿士,卿之有事也”,如西周金文中习见的“出入事人”,实在即出入办“事”的“人”。像小子生尊(集成6001)乃至“辬事于公宗”与“出入事人”并见,这都暗示金文中“事”可指“人”,或者说假“事”为“士”也有一定性。但该当指出的是,前述金文中作为男女通称的“士女”一样平常不写作“事女”,这也显示作为男子之通称,“士”也有无可替代之处。从另一方面说,“鄉事”或“卿事”中之“事”本指“事情”之“事”,这与指人的“士”也有明显差异。换言之,由于“鄉(享-服)事”这样的语义本源,“卿”与“事”的搭配是很早就固定的,并不会由于“事”与“士”通,就可以将个中的“事”更换为“士”而成“卿士”。传世文献中“卿士”之“士”,只是“事”的借单,从“鄉(享)事”当理解为“服事”这样的语义本源看,“卿士”一词实在也是不合文法的。这恐怕也是金文及简帛文献中“卿事”始终没有写成“卿士”的缘故原由。我们看直到春秋乃至战国早期,出土文献中“卿士”都是写作“卿事”的,如伯硕父鼎(铭图2438):“用孝用享于卿事、辟王、庶弟、元兄”, 曾卿事季宣匜(《铭三》41247)也有“曾卿事”,这是曾国的“卿事”。既明了“卿事”本义为“服事”以及作为成词的稳固,同样可以阐明前举清华简《祭公》篇及郭店、上博简《缁衣》所引“卿事”之“事”没有与前面的“嬖士”之“士”率尔趋同。从构词上看,“嬖士”乃散文式的偏正构造,指受“嬖”的“士”,重点在强调“人”,与“卿事”本义在强调“事”完备不同。而且,从高下文看,“嬖士”一语还隐有贬义,这与“卿事(士)”一样平常指高档级贵族就更不合了。
二、《厚父》的性子与周人的经典重修
既明了“卿士”一职实是由卜辞“鄉(享)事”演化而来,以及从“鄉事”到“卿士”的大致过程,我们就可以对包含这一职官的文献进行简捷的年代学判断。比如清华简《厚父》说“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陶下为之卿事”,这是讲皋陶为夏启之“卿事”,这里的“卿事”已经是明显成词化的职官。从上举卜辞及小子簋看,晚商只管“卿事”亦已成词为职官,但犹存在不少散文式的“鄉事”,或者说其时犹是散文化与成词并行的时期。但若说夏初即有职官化的“卿事”而皋陶任其职,无论如何是无法想象的,《厚父》的记载只能是后人追溯其事。如前所述,关于《厚父》的性子,学界目前有“夏书”“商书”“周书”平分歧见地,即以成词化的“卿事”来看,“夏书”说也绝不可信。虽然小子簋表明“卿事”于晚商已经职官化,彷佛“商书”说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但从《厚父》一篇对此职的闇练利用以及该篇措辞上与西周金文的诸多相合看,“商书”说实在也不可信。与此类似的还有《商颂·长发》篇,个中有云:“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旁边商王”,这是说降下伊尹为“卿士”以辅佐商王。说夏、殷之际就有了职官化的“卿士”,也不可信,这明显也是后人追溯口吻。古人谓“商颂”准确地说应为“宋颂”,于此可见有理。其余,“卿事(士)”成词化为职官之称后,还有进一步的简省,那便是单称“卿”而不言“事(士)”,从而衍生出诸如“上卿”“正卿”“孤卿”“六卿”等偏正词组。如果说“事”单称亦可指人的话,“卿”字在早期材料中则从来没有单称可指人的情形。从前述“卿事”的语义源于“享事”——“服事”来看,这本来也是很自然的,故单称“卿”来指人,只能是“卿事(士)”的进一步简省。上述由“卿士”简省而来的“上卿”“正卿”“孤卿”“六卿”诸称在传世文献如《左传》《国语》《周礼》等书中可以说极为常见,侧面亦可证这些文献的年代学特色。由此而及《夏书》之《甘誓》,个中云“大战于甘,乃召六卿”,我们前面既已说夏代不可能有职官化的“卿士”,故在此根本上进一步简省的“六卿”就更成子虚,以是《甘誓》之文亦当是后人的附会之词[26],而绝非夏代的实录。还有清华简《摄命》篇开头的“亡承朕鄉”,整理者最初读“鄉”为“向”,理解为“往昔”。学者多不同意此见地,或读“鄉”为“卿”[27],因此将“朕卿”理解为“我的卿士”,这明显是把“卿”算作“卿事(士)”的简省了。《摄命》篇年代为西周早期,其时“卿事(士)”不可能简省到单称“卿”的情形,故“朕卿”之说绝不可信[28]。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像《甘誓》这样不必是夏代的实录都可以是《夏书》,那《厚父》虽然“卿事”是后人的追溯之词,为什么不可以是“夏书”?这还要提到“夏书”归类的基本原则。那便是只管其措辞可以是后人追溯,即相对“晚出”,但篇中所讲内容则是夏代的,就像《甘誓》所讲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一样。类似例子还有《尧典》,本日大部分学者都已承认它也是后人追溯和整合,但其内容毕竟是讲尧时君臣谋议。以这个标准来看《厚父》,则所谓“夏书”解释显也有问题。该篇虽然提到禹、启、皋陶等“夏”时人,但他们只是铺垫,是“背景板”,它的重点还是当下的治民鉴戒,如“亦惟祸之攸及,惟司民之所取”“民心惟本,厥作惟叶”“民式克敬德,毋湛于酒”。尤其该当指出的是,作为“背景板”,它提到了“夏”的“亡厥邦”,也便是说它虽然也涉“夏”,但那只是陈迹,而非像《甘誓》这样的“当时事”。这一点可以参考《墨子·非命上》所引《仲虺之告》:“我闻于夏人矫定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这里夏的“龚丧厥师”与《厚父》的“亡厥邦”义近,解释在《仲虺之告》篇中夏也是“背景板”,而《仲虺之告》明属“商书”。以前朝为“背景板”来讲当下的治民鉴戒,还可举《尚书·召诰》。此篇提到“有夏”“有殷”都“既坠厥命”,此与《厚父》的“亡厥邦”义近,解释“有夏”“有殷”都是铺垫或“背景板”,该篇又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落脚点也是当下的治民鉴戒,此与《厚父》高度同等,而《召诰》明属《周书》。其余,《厚父》篇中王的口吻说“惟时余经念乃高祖……”,王的话同样解释时王与厚父的先人(王既称厚父的先人为“乃高祖”,明著“乃”字,这个王显然也不会是“夏王”)即夏史有明显的时序落差。且此篇厚父又自述云:“今民莫不曰:余保教明德,亦鲜克以悔”。厚父说“今民”“保效明德,亦鲜克以悔”,突出“民”的明德知化,这显然不会是“亡厥邦”或“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孟子·梁惠王上》引《汤誓》)时民众能说的话。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时王与夏事有明显的时序落差,那为什么不能是《商书》?这紧张是就该篇措辞上说的,学者们都已把稳到的《厚父》措辞与《尚书》周初诸篇及西周金文多有相合处。比如《厚父》的“今民莫不曰:余保效明德,亦鲜克以悔”与豳公盨铭文“民唯克用兹德,无悔”,语式及语义均极近,而豳公盨为西周中期器。上述这些情形解释,《厚父》绝不可能是“夏书”,而该当是《周书》。
当然,我们说《厚父》为《周书》,也无损于该篇作为夏史资料的史料代价。周相对付夏,中间隔了“商”这么一个朝代,但是周人的夏史影象从何而来?周人的夏史言说是否可信?这始终是历史、考古学者高度关注的话题。《厚父》篇最大的代价便是提示我们,作为夏的口述史载体,夏的后人如厚父者于周初仍旧存在。关于周初的夏人后裔,《史记·陈杞世家》载“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看来确非虚言。当然,“东楼公”之名与“厚父”不合,但《陈杞世家》又说东楼公之子名西楼公,但是东、西楼公之名似仅以地称,并非“厚父”这样的私名[29],其间信息缺失落太多,他们之间是何关系已经无法质言了,但夏人后裔于周初尚存该当是可信的。由《厚父》这样的周初“书”类文献可知,周灭商后时王曾问计于夏人后裔厚父,这种环境与《洪范》篇“王访于箕子”类似,而箕子是殷遗民。《厚父》篇王的口吻说“厚父!
我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这是在厚父发话之前,表明问计于厚父之时,周人对夏史已经有相称的历史认知。我们看《尚书》中周人对殷遗多士说“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士》),其对旧殷多方国说:“厥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崇乱有夏。……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钦,劓割夏邑。于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在夏”(《多方》),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周人对殷遗民大讲夏的兴亡史,解释这些夏史信息纵然在殷遗民那里也是公认的。周人原是商的臣民,这些历史信息,本不劳商灭之后夏人后裔来见告他们,它们在富商时该当便是“公共知识”。如《洪范》篇作为殷遗民的箕子对武王言:“……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正是富商旧人讲夏史。即便夏史作为“公共知识”早就存在,但时王仍要问计于厚父,解释在周人看来,厚父作为夏的后人其所言说无疑更直接、更有威信性。就像《洪范》篇武王“访于箕子”,而箕子是商遗民,其间道理是一样的。
虽然是周王问计于夏人后裔厚父之篇,但从篇中“王若曰”来看,恐怕亦有史官事后润色、整理的身分。由此我们还想指出,厚父所说的“定命不可忱”“民式克共心敬畏,畏不祥,保教明德”“民式克敬德,毋湛于酒……民亦惟酒用败威仪”如斯,与我们在传世《诗》《书》等经典文献中读到的“定命棐忱”“明德慎罚”[30]“罔敢湎于酒……用燕丧威仪”等等也基本同等。也便是说,厚父所讲与周人灭商后反复强调的定命靡常、敬德保民、谨慎于酒等思想基本同等。我们不敢说厚父的言说便是照着周人给定的“脚本”进行,但此篇的思想又很明显代表了周室的官方态度,因此也不能打消史官的润色和“选择”。当然,这些符合周人历史认知与统治思想的话出自夏人后裔厚父之口,无疑也加强了其威信性。这可能正是《厚父》篇问计于夏人后裔的现实考量:从“于周为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五年)的角度讲,厚父代表的是夏王朝,其典范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典范性就像武王问计于箕子,其篇曰“洪范”即题名“范”,它们都该当是周人典范性重塑之举。
说到周人的典范性重塑,就不能不提到《尚书》中的《夏书》。虽然题名“夏书”,本日恐怕没有人相信那是夏代的实录,学者多认为它出于后人的整理,系后人对夏史的追溯和整合,而非夏时经典原来当时还有留存。因此,如果说《周书》特殊是周初八诰基本上来自于周人的原始文件的话,《夏书》的性子显然不会是夏时的原始文件,它们应源于周人对夏的经典重修。这种经典重修从可利用的材料看,既有自古相传的关于夏史的“公共知识”,也有类似厚父这样夏人后裔的口述史资料,周室史官据此将他们整合成篇。由于非夏时的原始文件,周人对《夏书》的经典重修实质上可视为文献学上的“依托”,这种“依托”特色可参考清华简中的《程寤》、《保训》等篇。从清华简的这些篇目看,周人对“依托”这种经典重修技能的利用该当是很自觉、很纯熟的。而且,周人这种经典重修形式上虽是“依托”,但涌现的绝对年代可能也并不晚。李学勤师长西席已就《程寤》中措辞与《尚书·吕刑》的相合指出过这一点[31]。我们还可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左传·襄公四年》记周之太史辛甲云:“《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尽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虞箴》如是,可不惩乎?”,这是周室虞官立意于箴诫田乐的文体。个中的“德用不扰”之“扰”,晚近不少学者都已认识到大盂鼎铭文“有祡烝祀,无敢扰”、启卣(集成5410)“启从征,谨不扰”、训匜(集成10285)“自今余敢扰乃小大史(士)”之“无敢扰”“谨不扰”“余敢扰”与之义近,解释这是当时习用之语,而《虞人之箴》又为传世文献所仅见者。大盂鼎、启卣、训匜属西周早、中期器,侧面解释《虞人之箴》的早出,但其文风较之《周书》中的命诰浅近不少。古人习气以文体差别论时序之异,这很片面,实际上它们完备可能是“共时”的。当初王国维即指出《虞夏书》中之《尧典》、《皋陶谟》、《甘誓》等篇虽“笔墨稍夷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但又认为“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32],就没有将文风与时序大略划等号,实际上也是对周人以“依托”的手腕进行经典重修的恰当估计,今由清华简《程寤》、《保训》等篇看,王氏的估计还是很有预见性的。实在,即周初的命诰中同样也有述“夏史”内容,如《召诰》篇有:“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多士》篇有“有夏不适逸……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立政》篇有:“古之人迪惟有夏,……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陟……”,都属周人讲夏(殷)时势,此与“依托”的异时性时序逻辑实质上并无不同,而绝对年代同样却很早。其余,《虞人之箴》因此韵体文讲夏史,这可参照《左传·哀公六年》载《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落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33],文体上两者可以说非常靠近。后者明署“夏书”,而前者虽用“夏史”劝谏时王(与《厚父》类似),但显然辛甲没把它算作“夏书”。哀公六年讲陶唐氏兴衰,属后人“依托”但却谓之《夏书》:作者与所讲时期明显存在间隔。依此事理,绝对年代很早的《虞人之箴》讲“夏史”实在同样可视为周室虞官的“依托”:就“依托”这种经典重修办法来讲,它们确有共性。如果有人将《虞人之箴》截取而谓之“夏书”,那真的是真假莫辨。
正由于多是“依托”而非官方的原始文件,现存《夏书》中的大部分内容较之佶屈聱牙的周初命诰来说,确如王国维所说“夷易简洁”。这种“夷易简洁”的一大特色便是还常见“往后当先”的名物疏漏。如明属《周书》的《厚父》陈说夏史时却用到了“卿事”一词,《夏书·甘誓》中乃至还涌现了“六卿”,这更是在“卿士”根本上的进一步简省,绝不可能是夏代的东西。类似例子还可举《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啬夫”一职晚近秦汉简牍中多有创造,虽然《左传》所引解释此职先秦即有,但要说夏代已有此职也是不可想象的。此处“夏书”所记明显也是“往后当先”,定出“依托”无疑。其余,《左传·襄公十四年》亦引《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个中描述的臣工各以其技谏诤,案之《国语·周语上》,这可能本来是周代才完备的制度。名物疏漏之外,措辞上的“夷易简洁”就更为明显了,试看《左传》中所引“夏书”:“《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34];“《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35];“《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落不经’”[36]、“《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37]我们前面说这种“依托”的经典重修就绝对年代看可能也不晚,但就《左传》所引上述“夏书”看,其相对晚出该当是很明显的。《吕氏春秋》引《夏书》又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38],切实其实像大口语。由此,我们认为《尚书》中的“夏书”,不但是周人用“依托”手腕进行的经典重修,而这样的重修也是“历时态”的。这也与“书”类文献一向的不断充足、“叠代”相同等。比如前举清华简《程寤》篇见今《逸周书》,而《逸周书·大开武》云“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李学勤师长西席谓此即暗引《程寤》[39],则《大开武》实可视为对《程寤》的“叠代”,故在《逸周书》同一部书中,个中篇目之时序已有明显落差。再如《周书》中既有周初八诰,也有《文侯之命》和《秦誓》,虽不是篇目对位“叠代”,但时序差异也是很明显的。《礼记·大学》又载:“……《康诰》曰:‘惟命不于常!
’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落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措辞相对浅近的《楚书》明显较属《周书》的《康诰》要晚,舅犯的辞吐就更晚了,但《大学》作者却把他们等量齐观。我们认为“夏书”也该当是搜集来源多途、不同时期讲“夏史”文献而成。这么说就意味着,“夏书”的归类和作为整体、独立板块的自觉,可能也是比较晚起的。从朝代时序来说,由夏、历商,至周,但就经典天生的顺序来说,我们认为实在大体是逆序的过程:“周书”最早,“夏书”相对最晚。《墨子·非命下》有个说法:“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四代之“记”实在即四代之“书”,而“虞夏”还要后于“商周”,这种奇特顺序恐怕也是有深义的。正由于“夏书”的自觉相对较晚,就典范性来说恐怕也不能与《周书》比较。由此还要提到古人曾经指出的一个事实,那便是“尚书”类文献中,也以《夏书》亡佚、消逝得最多,这并非由于它们更久远,实由于“夏书”相对晚出、较晚自觉,由此导致典范性上远逊《周书》的缘故。如果说周人对《夏书》的经典重修是故意为之的话,而《夏书》的消亡最甚恐怕更多是流传领域的自然选择。
注释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250);“古笔墨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方案项目(G3453)。
作者简介:宁镇疆,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先秦史、出土文献与古代思想文献研究。
[2] 持“夏书”说者以郭永秉为代表,参其《论清华简〈厚父〉应为〈夏书〉之一篇》,《出土文献》第7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18页。持“商书”说者可参张利军《清华简〈厚父〉的性子与时期》,《管子学刊》2016年第3期;王晖:《清华简<厚父>属性及时代背景新认识——从“之匿王乃渴失落其命”的断句释读提及》,《史学集刊》2019年第4期。持“周书”说者可参李学勤《清华简〈厚父〉与〈孟子〉引〈书〉》,《深圳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程浩:《清华简〈厚父〉“周书”说》,《出土文献》第5辑,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145页;刘国忠:《也谈<厚父>的撰作时期与性子》,《扬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3] 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本文简帛文献释文一样平常径用宽式。
[4] 释文参侯乃峰《上博楚简儒学文献校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60页。
[5] 如夨令方尊、方彝(集成6016、9901)及近出韩伯丰鼎都是如此。
[6] 张富海:《清华简<系年>通假柬释》,载李守奎主编:《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447页。下引张说俱见该文。
[7] 王挺斌:《战国秦汉简帛古书训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19-121页。
[8] 于省吾引“应子容”之说谓“庆士”即“卿士”,参氏著《双剑誃吉金文选》,载《于省吾著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3页。
[9] 张富海:《清华简<系年>通假柬释》。
[10]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中西书局,2017年,第146页。
[11] 海天游踪:《清华七〈越公其事〉初读》,武汉大学简帛网“简帛论坛”,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4566&page=10,2017年4月30日。
[12] 子居:《清华简七<越公其事>第十、十一章解析》,中国先秦史网,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915514358.aspx,2017年12月13日。
[13] 学者或将“行李”理解为并列构造的同义连言(兰碧仙、叶玉英:《据清华简再谈“行李”之“李”》,载《中国笔墨研究》第28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8页),恐非是。
[14] 关于早期文献中“人”与“士”作为他称及常可互换,拙文《西周金文中的“出入事人”研究》(《青铜器与金文》2023年即刊)有详细谈论。此文曾于2022年12月22日应华东师范大学之邀做线上讲座,听众提问环节承吉林大学许世和博士告:战国兵器铭文亦常以“冶事(士)”与“冶人”对举,不惟可以证成拙说,亦足证直到战国晚期用“事”以指人仍是很常见的。
[15]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三卷》卷下,东方学会1927年印;王国维:《释史》,载《王国维手定不雅观堂集林》(黄爱梅点校),杭州:浙江教诲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
[16] 郭沫若:《卜辞通纂》,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89-490页。
[17] 唐兰:《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文考释》,载《唐兰师长西席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第6页;李学勤《卿事寮、太史寮》,《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18] 参于省吾主编:《甲骨笔墨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78页姚孝遂按语。
[19] 蔡哲茂:《释殷卜辞的字(簪)》,《东华人文学报》第十期,2007年。
[20] 黄天树:《殷墟甲骨文助动词补说》,《古汉语研究》2008年第4期。
[21] 陈剑:《释“”》,《出土文献与古笔墨研究》第三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2] 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66页。
[23] 陈剑:《清华简与<尚书>字词合证零札》,载《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李学勤师长西席八十寿诞纪念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211页。
[24] 吴闓生:《诗义会通》,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240页。
[25] 董珊:《重论凤雏H11出土的殷末卜甲刻辞》,载蔡玫芬主编:《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第338页。
[26] 《墨子·明鬼下》引《禹誓》作“王乃命旁边六人”无“卿”字,但其下文又说“且尔卿、大夫、庶人……”(今本《甘誓》无此内容),则“卿”明显已单称。学者谓“六卿”系后来妄改(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855页),显然失落察于《墨子》的“且尔卿、大夫、庶人”。
[27] 许文献持此说,拜会刘信芳《清华藏竹书<摄命>释读》,载《清华简<摄命>研究高端论坛论文集》,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央2019年,第56页。
[28] 《摄命》此处的“鄉”当读为“享”,参拙文《清华简<摄命>“亡承朕鄉”句解——兼说师询簋干系文句的断读和理解问题》,《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2期。
[29] 刘国忠:《也谈<厚父>的撰作时期与性子》。
[30] 《墨子·非命下》引《禹之总德》亦有:“不慎厥德,定命焉葆?”,虽题名“禹”,但“慎德”不雅观念亦与周人同。
[31] 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32] 王国维:《古史新证》,长沙:湖南公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
[33] 清华简《四告一》云:“(司慎皋繇)……惠汝度天心,兹德(天德)用歆,名四方,氐尹九州,夏用配天……”(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第110-111页),语式与哀公六年引《夏书》及《虞人之箴》都很靠近。
[34] 参僖公二十七年,文见今《益稷》篇。
[35] 参文公七年,伪古文采入《大禹谟》篇。
[36] 参襄公二十六年,伪古文采入《大禹谟》篇。
[37] 参哀公十八年,伪古文采入《大禹谟》篇。
[38] 《吕氏春秋·有始》。
[39] 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