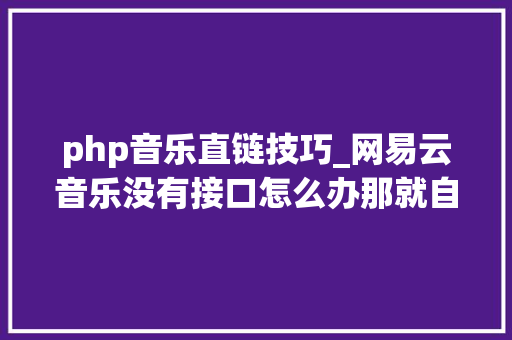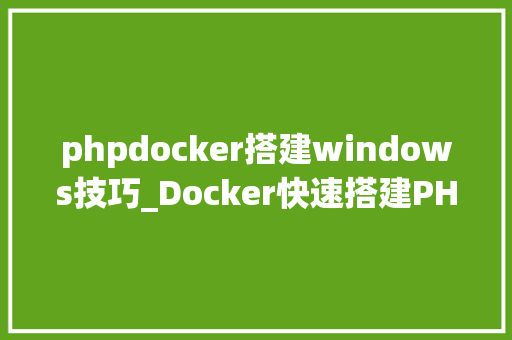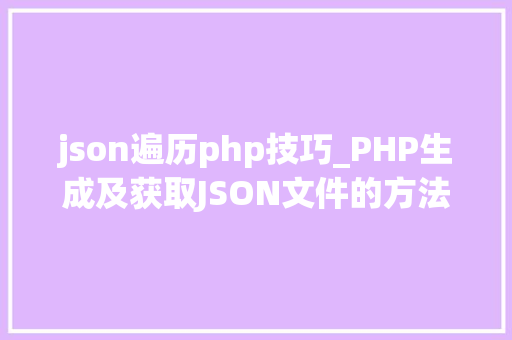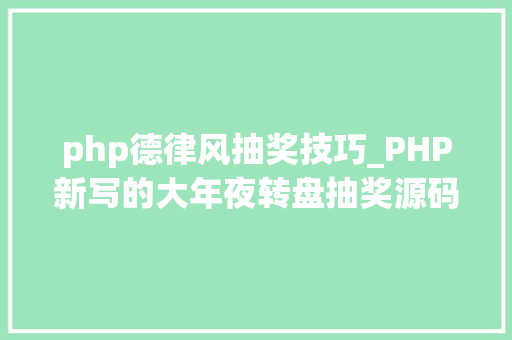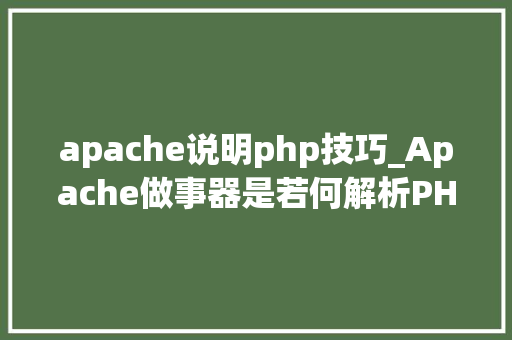一、《赵正书》与传世文献记载的异同
《赵正书》全文,整理者已经做了根本性的考释事情。对付《赵正书》与传世史乘的异同,整理者也进行了很好的比较,指出:二世杀扶苏、蒙恬时子婴谏言,李斯自呈七罪,与传世文献(紧张是《史记》)大体附近;而《赵正书》中胡亥继位,以及章邯杀赵高,与传世记载不同;李斯临终谏言及子婴谏言,传世文献未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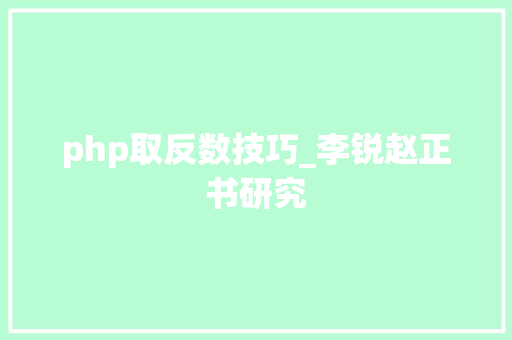
《赵正书》的开篇与《史记》有很大不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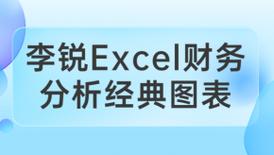
昔者,秦王赵正出游天下,还至柏人[2]而病。垂死,喟然流涕长太息,谓旁边曰:“定命不可变欤?吾未尝病如此,悲□……”……而告之曰:“吾自视定命,年五十岁而去世。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岁矣。吾当以今【岁】去世,而不知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以变气易命,不可欤?今垂死,几去世矣。其亟昼夜输趋,至白泉之置,毋须后者。其谨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
病即大甚,而不能前,故复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纷争,争侵主。吾闻之:牛马斗,而蚊虻去世其下;大臣争,齐民苦。吾哀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去世且不忘。其议所立。”丞相臣斯昧去世顿首言曰:“陛下万岁之寿尚未央也。且斯非秦之产也,去故下秦,右主左亲,非有强臣者也。窃善陛下高议,陛下幸以为粪土之臣,使教万民,臣窃幸甚。臣谨奉法令,阴修甲兵,饬政教,官斗士,尊大臣,盈其爵禄。使秦并有天下,有其地,臣其王,名立于天下,势有周室之义,而王为天子。臣闻不仁者有所尽其财,毋勇者有所尽其去世。臣窃幸甚,至去世及身不敷。然而见疑如此,臣等尽当戮去世,以报于天下者也。”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去世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3]
这里记载李斯请秦始皇立胡亥为代后,其后紧接着讲:“王去世而胡亥立,即杀其兄扶苏、中尉恬。大赦罪人,而免隶臣高以为郎中令。因夷其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4]此时的赵高尚为隶臣,被二世立为郎中令。这与《史记》中赵高主导沙丘之谋有明显的差别。其下记载胡亥欲漫游天下及杀扶苏、蒙恬,子婴进谏,简文的这段内容与传世文献有附近者:
又欲起属车万乘以抚天下,曰:“且与天下鼎新。”子婴进谏曰:“不可。臣闻之:芬茝未根而生凋旾〈喷鼻香〉同,天地相去远而阴阳气合。五国十二诸侯,民之嗜欲不同而意不异。夫赵王巨杀其良将李微[5]而用颜聚,燕王喜而轲之谋而背秦之约,齐王建遂杀其故世之忠臣而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终以失落其国而殃其身。是皆大臣之谋,而社稷之神零福也。今王欲一日而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之:轻虑不可以治固〈国〉,独勇不可以存将,同力可以举重,比心壹智可以胜众,而弱胜强者,高下调而多力壹也。今国危敌比,斗士在外,而内自夷宗族,诛群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秦王胡亥弗听,遂行其意,杀其兄扶苏、中尉恬,立高为郎中令,出游天下。[6]
赵高是在胡亥杀了扶苏、蒙恬之后才担当郎中令。再其下为李斯自呈七罪,与传世文献大体附近:
后三年,又欲杀丞相斯,斯曰:“先王之所【谓】牛马斗而蚊虻去世其下,大臣争而齐民苦,此之谓夫!
”斯且去世,故上书曰:“可道其罪,足以去世欤?臣为丞相卅余岁矣,逮秦之迹〈陕〉而王之约。始时,秦地方不过数百里,兵不过数万人。臣谨悉意壹智,阴行谋臣,赍之金玉,使游诸侯。而阴修甲兵,兵饬斗士,尊大臣,盈其爵禄。故终以胁韩而弱魏,又破赵而夷燕代,平齐楚,破屠其民,尽灭其国而虏其王,立秦为天子者,吾罪一矣。地非不敷也,北驰胡幕,南入定巴蜀,入南海,击大越,非欲有其王,以见秦之强者,吾罪二矣。尊大臣,盈其爵禄,以固其身者,吾罪三矣。更刻画斗桶,度量壹,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者,吾罪四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者,吾罪五矣。治驰道,兴游不雅观,以见王之得志者,吾罪六矣。缓刑罚而薄赋敛,以见主之德,众其惠,故万民戴主,至去世不忘者,吾罪七矣。若斯之为人臣者,罪足以去世久矣。上幸而尽其能力,以至于今,愿上察视之。”秦王胡亥弗听,而遂杀斯。[7]
再下为李斯临终谏言及子婴谏言,传世文献未载:
斯且去世,故曰:“斯则去世矣,见王之今从斯矣。虽然,遂出善言。臣闻之曰:变古乱常,不去世必亡。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所谓变古而乱常者也。王见病者乎?酒肉之恶,安能食乎?破国亡家,善言之恶,安能用乎?桀登高知其危矣,而不知以是自安者;前据白刃自知且去世,而不知以是自生者。夫逆天道而背其鬼神之神零福,灭其先人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中人之功力,而求鼎新者,王勉之矣。斯见其殃今至矣。”秦王胡亥弗听,遂杀斯。子婴进谏曰:“不可。夫变俗而易法令,诛群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使以法纵其欲,而行不义于天下臣,臣恐其有后咎。大臣外谋而百姓内怨。今将军章邯兵居外,卒士劳苦,委输不给,外毋敌而内有争臣之志,故曰危。”秦王胡亥弗听,遂行其意,杀丞相斯,立高,使行丞相、御史之事。未能终其年,而果杀胡亥。将军章邯入夷其国,杀高。[8]
全文本来至此结束,勾号“”是表示结束的标志。但此篇在勾号后还有一句评语:“曰:‘胡亥所谓不听谏者也,立四年而身死国亡。’”[9]这解释《赵正书》曾经有过一个流传过程,后来的抄者为了某种目的,在全文结束后加了评语。也便是说,《赵正书》的成书,比北大简的韶光下限要早,整理者推断:“撰写年代为西汉初期的可能性较大。”[10]而评语者彷佛也未对胡亥继位的合法性有异议。《赵正书》没有突出赵高的浸染,很多事彷佛都是胡亥自己的主张,并且子婴几次再三进谏。此篇所述赵高为隶臣,李斯发起以胡亥为代后,与《史记》所载的沙丘之谋有明显的差异。
《赵正书》既然与传世文献所记事有同有异,大略地以之为真或伪就不足严谨。我们先看看除了秦始皇临终立胡亥之外,《赵正书》给我们供应了什么信息,以有助于判明其代价。
二、律令与故世之藏
《赵正书》记载胡亥登基后,“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李斯谏言中再次提及“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和“燔其律令及中人之功力”,子婴谏言中说“变俗而易法令”,这些话恐怕不能轻易放过。秦以法立国,胡亥燔其律令,变易法令,此事文籍没有详细记载。《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法令诛罚日益刻深”,[11]《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二世“用法益刻深”,[12]可谓语焉不详。《赵正书》则可以供应一些宝贵的历史信息。
首先,陈胜、吴广叛逆时,其情由是“会天算夜雨,道不通,度已失落期。失落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去世,举大计亦去世,等去世,去世国可乎?’”[13]然而比来学者们根据睡虎地秦简、张家山二年律令,指出“失落期,法皆斩”不符合秦朝的法律。李开元师长西席认为陈胜可能是贵族后裔,[14]因此他该当识字,能打仗、理解秦国法律;同行的其他人也可能理解法律规定。只有过去的法律条文被烧毁,国家行事不依故法而行,才能涌现《史记·李斯列传》所记载的“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二世“用法益刻深”,陈胜所说的“失落期,法皆斩”才可能属实。
其次,刘邦攻占咸阳之后,与秦民“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去世,伤人及盗抵罪。余悉撤除秦法……秦人大喜”,[15]《新序·善谋下》也记载刘邦“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16]这些记载给人的印象是秦法严苛,刘邦于是约法三章。对付以安民为目的的刘邦来说,恐怕没有比依秦故法而撤除严刑峻法更简便的方法了;而秦朝的法律里面,也不会对“杀人者去世,伤人及盗抵罪”有异议。因此,实际情形很可能是秦的故法已经烧毁,大家又不愿遵守秦二世的严刑峻法,故刘邦规定了最基本的三条原则。
再次,萧何改定《九章律》,可能也与秦的律法被烧毁及行用秦二世的法律有一定关系。由出土文献可以看到,汉律在很大程度上与秦(始皇期间)的律法有延续性,这也解释刘邦的“约法三章”并非是别出心裁而与秦法不同。
其余,更值得重视的恐怕是“故世之藏”。历代关于秦焚书,更多地考虑由李斯发起而得到秦始皇批准的挟书律。按照挟书律,“博士官所职”者,即官方,仍可藏书。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标举《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之义,以“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17]为刘歆之伪说,[18]甚至连启示了康氏的廖平都反受其影响,将其说写入《古学考》之中。[19]后来廖平的弟子蒙文通细数秦廷称引六艺经籍之事,认为“孔子之术,诚不因坑焚而隐讳,亦不待除挟书之律而显著”。[20]但由《尚书》等的残缺不丢脸出,秦的官方藏书已残缺。据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一《秦燔灭文章》及方回《续古今考》卷六、卷二九所载,吕东莱曾说:“萧何独收图籍而遗此,惜哉”,[21]吕东莱认为萧何入关收图籍时没有网络官方藏书。萧参《希通录》则谓“天下之书虽焚,而博士官犹有存者。惜乎入关收图籍而不及此,竟为楚人一炬耳,前辈尝论之”,[22]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秦之焚书,焚天下之人所藏之书耳。其博士官所藏,则故在。项羽烧秦宫室,始并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往后之学者咎萧何不能于收秦图书之日并收之也”。[23]萧、胡之论,表明以前之学者多认为秦不焚博士官之书,而经籍亡佚之过,逐渐转移到了萧何、项羽身上。此后持附近论点者犹多。[24]
现在由《赵正书》的记载来看,很可能是胡亥烧毁了秦的官方藏书,以是《史记·萧相国世家》说“(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25]萧何入关收图籍时,只有地理、户口这一类实用的东西;当时存在的律令,显然已经不全,或者只是胡亥新颁布的律令,以是刘邦不得不约法三章,萧何也要更定《九章律》。
蒙文通举“蒙恬说《金縢》之传,蒙毅陈《黄鸟》之说”,[26]以证“孔子之术,诚不因坑焚而隐讳”,[27]所举两事,俱见《史记·蒙恬列传》。然而蒙毅未明引《黄鸟》,其所说“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去世,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28]或本无“三良而去世罪”五字,[29]故所言未必是《秦风·黄鸟》;蒙恬所述周公言行与《金縢》有差别,虽引有“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不见今《尚书》及《逸周书》),[30]但这些都是蒙氏兄弟临去世前与青鸟使之语,并非上书陈情。《史记·李斯列传》记胡亥以韩非之言问李斯,李斯则以申子、韩子之语、商君之法以阿胡亥之意。这些属于诸子百家语的东西,在胡亥“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后,即便有人称引诗书百家语,那也只能是口传,不久终将亡灭。当然,也有可能商鞅、申不害、韩非这些人的著述,符合秦朝统治的意识形态,不会以古非今,不在焚毁之列。所幸二世胡亥统治不久,很多口传、壁藏的书到了汉初还得以保存。但是与先秦比较,许多主要的文籍残缺不全,很多学派的传承被截断,文化的丢失非常大。
此外,《赵正书》记载胡亥“又欲起属车万乘以抚天下,曰:‘且与天下鼎新’”,李斯临终前说及“夫逆天道而背其鬼神之神零福,灭其先人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中人之功力,而求鼎新者,王勉之矣”,而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记载:“天下失落始天子,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事及箸(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以元年与黔首鼎新,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正)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31]三处“鼎新”也是《史记》所没有的内容。
三、胡亥继位的合理性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说“朕奉遗诏”,但是不少学者认为这个遗诏是《史记》所载沙丘之谋的矫诏,二世之言不可信。[32]那么胡亥是否是秦始皇的合法继续人呢?鄙意这个问题,该当从更大的背景来剖析,要从秦始皇晚年的统治术谈起。
秦统一后,百家后学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分封等说均被否定,乃至焚书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坑儒事宜的起因为: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尸位素餐,莫敢效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震怖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去世。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吉人,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昼夜有呈,不中呈不得安歇。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33]
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昼夜有呈,不中呈不得安歇”,彷佛秦始皇是一个事必躬亲的独裁者。但是此事的前因,却是: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去世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不雅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去世。始天子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34]
很显然,此时秦始皇虽然决事,但是已经自称真人,隐匿自己的所在,追求以所谓的恬倓(恬淡)之法治天下。对付透露其行藏和言语者,罪去世。
如果说此前的秦始皇是独裁、专权的话,之后已有所改变。群臣已不知秦始皇的所在,何来“上至以衡石量书,昼夜有呈,不中呈不得安歇”呢?即便侯生、卢生也未必能知晓。可见司马迁所载侯生、卢生之说,已有自相抵牾之处。
真人之说与以恬淡之法治天下,所依循的多是《老子》及干系学说。秦始皇慕求永生,而古代早有人据《老子》求永生,如张家山汉简《引书》简111云:“治身欲与天地相求,犹橐籥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35]便是根据《老子》第5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36]而来。《庄子》中记载有很多“真人”的神通之说,如《庄子·大宗师》载:“古之真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37]所言与卢生说附近,而《庄子·天下》篇说“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38]又《老子》第31章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39]须要把稳的是,此处之“恬淡”,郭店简作“铦”,帛书甲本作“铦袭”,乙本作“铦忄龍”,北大简本作“恬偻”,虽然就通假而言可以读为“恬淡”,[40]但当前很多学者并不这么释读,而是从兵刃的铦利方面来考虑。不论如何,此处是论用兵,卢生之言却将之转换为治国之道,显然《老子》的思想已经被转化。《论衡·自然》篇说:“黄、老之操,身中淡泊,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41]始皇所用,恐怕正是某种黄老之术,或带有黄老特色的治术。《韩非子·忠孝》篇讲“世之所为义士者,虽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42]恐怕便是秦始皇臣子中对始皇用黄老之术的诤谏。[43]
稽核秦始皇晚年的统治办法及活动,不难创造,他实在因此《老子》的恬淡和永生为目标,详细统治术是申子的“术”,君无为而臣有为。除了术之外,当然还有法和势,此时秦制的根本便是韩非子所说的法、术、势,因此法一民,以势迫人,而君则用术稽核群臣。商鞅之法早已在秦实施多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增加了对术和势的重视,正如《外储说右下》所指出的:“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44]以是我们看秦始皇在宫中则让人“莫知行之所在”,外出巡游则设有正副车,其路线恐怕也少有人知晓,正是“身在深宫之中”和“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秦始皇漫游天下,后来则和寻求永生有关,但很类似古代的巡狩。巡狩有稽核地方官吏的内容,秦始皇应该也会循名责实稽核官员。
北大简《赵正书》说秦始皇临去世前选定二世为继续人,而《史记》等所载则是始皇本选定扶苏为继续人。胡亥与扶苏的差异,值得负责磋商。
史载扶苏的辞吐并不多,紧张是“坑儒”时,他劝谏过秦始皇,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结果“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45]显然,扶苏的政见和秦始皇不合,不得始皇之心。相反,秦始皇末了一次出游时,“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46]胡亥对付秦始皇的行事,很有兴趣,秦始皇也赞许带着他。《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始皇有二十余子,宗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余子莫从。”[47]可见扶苏多次触怒秦始皇,秦始皇对扶苏和胡亥的态度差异,一览无余。
从扶苏所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来看,他对付求仙药的术士都如此宽容,扶苏若继位,可能实施偏于怀柔的政策,不会再连续实施严刑峻法,以求安抚百姓。但是这一方法恐怕和秦一向的国策不合,也和秦始皇据终始五德说所确立的国策不合:“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48]倒是胡亥统治百姓的方法,是继续了秦始皇的“策略”,他说:“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49]便是要连续用法术势来掌握天下。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记载:“以元年与黔首鼎新,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正)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由此可知,二世胡亥开始登基时也想以宽柔之法来收买民气,这很可能出于李斯的建议,《赵正书》中,他自数其罪第七时说“缓刑罚而薄赋敛,以见主之德,众其惠,故万民戴主”;[50]《赵正书》中也言及曾“大赦罪人”。但文告中“解除流罪”等事情,其施行韶光有多久,是有待考验的。根据《赵正书》中李斯所言,“夫逆天道而背其鬼神之神零福,灭其先人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中人之功力,而求鼎新者,王勉之矣”,所谓“宗庙事”,恐怕包括诛灭群公子,“自夷宗族”;“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则可能不久之后就采取赵高所建议的“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51]即李斯所言“燔其律令”,甚至“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用法益刻深”。后者恐怕才是《赵正书》中李斯所批评的“变古乱常,不去世必亡”的重点所在。以是“解除流罪”等宽柔政策,恐怕只不过是“鼎新”的一时姿态,这一政策很快就转变了。
政策转变的背后,看起来有李斯和赵高的影响。二世天子巡游之后,赵高进谏,一说:“‘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登基,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52]二劝“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53]当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说盗贼益多时,二世称引韩非之言说:“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今朕登基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效忠力,何以在位?”这是用循名责实之法敲打李斯等,之后“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54]而且明确责怪李斯等要“罢先帝之所为”。李斯阿二世之意,说:“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礼服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55]仍旧强调用法术势来管理群臣,实际上表明他已失落宠,无法再影响二世天子的政策。
二世天子的行事,虽然与赵高的进谏有很大关系,但是其行事之由来,还是和秦始皇的统治术有关,“不闻声”,“常居禁中”,和秦始皇晚年之法附近,颇有模拟、遵照秦始皇之意。只是韩非子曾在《难势》篇已经指出势只适宜中人来利用,“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56]而胡亥正好便是依赖赵高不能自主的庸才,被赵高所掌握,终极一定失落败。
胡亥的这种统治术,如果打消赵高的建议,是否比扶苏的政治空想差呢?我们不妨看看汉初的统治术。如前文所说,术和势都与《老子》之说有一定关系。以恬淡无为为目标、君无为而臣有为为方法、法术势兼用的统治术在秦始皇末期曾实施过。至汉统一天下之后,在汉承秦制的大背景下,行何种统治术,是汉朝统治者要考虑的问题。当刘邦诛灭背叛的王侯之后,曹参选用一个能对秦制进行微调的统治术——河上丈人一系的黄老之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概河上丈人是一种为了与卢生平分离派系的杜撰。河上丈人一系的黄老之术,虽然既讲黄也讲老,但黄帝之说显然只是后人的饰辞,而《老子》却有确切不易的文本存在并流传几百年,因此其核心仍旧是《老子》。这个黄老之术,是曹参多方搜求而得的,并且和儒生之言进行了比较,又在齐经由了实验,被证明行之有效。《曹相国世家》载:“参尽召长老诸生,问以是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大家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寂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57]
曹参任丞相后,也是“萧规曹随”,[58]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不妄为多事,汉政权才逐渐稳定下来,民心归附。但所谓萧规曹随,更多的是汉承秦制,律法方面仍多承秦法,这表明汉政权并不比秦“怀柔”多少。刘邦著名的《大风歌》所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59]依旧是要猛士来威慑四方,以保政权稳固。因此,扶苏的政治空想,实际上在汉初也不可能“实施”。
历不雅观前尘往事,对付通过战役取得的政权来讲,其安集百姓无非宽猛二途,但首先是对付内、外部怀有异心及可能怀有二心者进行打击和威慑,当然也包括在一定条件下的收买和安抚,否则政权可能被颠覆;其次才是用怀柔政策对“顺民”进行安抚。由于政权不稳,就没有安集百姓的余地。因此,胡亥虽然糊涂,但毕竟还一度效仿秦始皇,而扶苏则未尝不是迂阔。胡亥后来专信赵高,扶苏则听不进蒙恬的劝谏。扶苏得诏书赐去世后立即***,正解释其之不成熟。胡亥的差错,则紧张是用法比秦始皇期间还要刻深。两比较较,以目前的材料来看,扶苏之于胡亥,并无绝对的高下之别,扶苏尚失落之迂阔。从这方面来看,《赵正书》讲在秦始皇巡游过程中突生变故的仓促情形下,经由李斯的发起,让胡亥继位,是通情达理的。[60]
四、《史记》有关史事剖析
与《赵正书》及秦二世元年文告相“抵触”的紧张文献,是《史记》环绕“沙丘之谋”而来的干系记载,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如赵高所言“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宗子书。宗子至,即立为天子,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61]陈胜说:“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62]叔孙通也说:“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63]但与此相违背的记事也有:
一是杀蒙毅之时,胡亥拟定的罪名是“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去世,亦甚幸矣。卿其图之!
”蒙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
非敢饰辞以避去世也,为羞累先主之名。”[64]
这一处对话表明,秦始皇曾故意立胡亥为太子,蒙毅曾经阻难。但蒙毅在答词中虽为自己解脱,也解释了“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的事实。
蒙毅大概确实曾阻难秦始皇立太子,李斯则长于见风使舵,《赵正书》中记载秦始皇要他推举继嗣人选,他就先说自己被秦始皇疑惑不忠,到秦始皇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他才和冯去疾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
二是所谓秦始皇要立扶苏为太子,但是诏书的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与丧会咸阳而葬”;[65]《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66]赵高对胡亥的说辞是“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宗子书。宗子至,即立为天子,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对李斯的转述则是“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67]如果单看《本纪》和《李斯列传》的正面说辞,是看不出立扶苏为继嗣之意的,反而像是发给一样平常公子、大臣的诏书。我们看赐扶苏去世的诏书,姑不论是否为秦始皇所发,则特殊长且详细:“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诋毁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昼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
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去世,以兵属裨将王离。”[68]
或据《秦始皇本纪》中“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69]认为“《李斯列传》作‘为书’,中无‘玺’字。此有‘玺’,谓玺及书也。《李斯列传》云‘书及玺皆在赵高所’,又云‘所赐宗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皆可证玺书为二物。此既言玺及书,则‘为’当训‘以’,谓乃以玺书赐公子扶苏。‘为’非‘作为’之为,玺书二字平列,非封书以天子玺也。”[70]但《本纪》上文“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后,明言“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71]以是恐怕并无将传国玉玺一并给扶苏之事。
因此,司马迁恐怕无从知晓绝密的所谓沙丘之谋及某个给扶苏的遗诏,只能移用给一样平常公子、大臣的诏书,又借用赵高之口,把《本纪》中的“与丧会咸阳而葬”,转变为《李斯列传》中的“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
然而据《赵正书》来看,立胡亥是李斯和冯去疾的发起,到胡亥继位后,才“免隶臣高以为郎中令”。而且,李斯所谓“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诏期群臣”恐怕正对应“与丧会咸阳而葬”。
因此,据《赵正书》来看,此时赵高还是犯人,无从参与沙丘之谋;然而据《史记》来看,赵高主导了沙丘之谋,二说不可并立。但如果求同存异,则不难疑惑“与丧会咸阳而葬”不是专门给扶苏的继位“遗诏”,而是给一样平常公子、大臣的诏书。如此一来,《赵正书》说李斯建议“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对付李斯而言,于公于私,都是合理的选择,也是秦始皇无法疑惑李斯之忠心的发起,恐怕也是秦始皇不得不接管的建议。由于秦始皇并未立储,而正好随身带着胡亥,他已经不可能面授扶苏继位,那么不管诏书有多高威信,旁人都能疑惑其合法性。如果扶苏以诏书加蒙恬的军队来确定威信,那么国家很可能将会陷入分裂。
此外,藤田胜久、李开元师长西席曾指出扶苏的母亲,可能来自楚国王室。[72]这一推测很有可能性。对付反感谶纬预言的秦始皇而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73]的预言,恐怕很早就让秦始皇疏远了扶苏,这或许也是扶苏接到伪诏后立即自尽的缘故原由之一。而“亡秦者胡也”的预言,则让秦始皇“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74]并没有疑惑到胡亥头上。从这一点来看,《史记》也为胡亥的顺利继位留下了伏笔。
总之,秦统一天下,却二世而亡,后世有隋与之比肩,个中恐怕存有某种一定性。虽然两个朝代都在继嗣的问题上有一些遗憾,但即便是扶苏、杨勇继位,历史也未必会改不雅观,由于叛乱的种子并未肃清,汉唐立国之初都四处征伐平叛。就《赵正书》与《史记》的记载比较而言,《史记》所讲“沙丘之谋”虽然比较圆满,但可能属于一家之言,有很多内容或出自虚构。在笔者看来,流传中的《赵正书》,倒可能反响了很多历史事实。
当然,目前的材料及笔者的论述,对某些学者而言,还不敷以让其相信《赵正书》之言。然笔者所提证据,可备一说。两说并立,以待将来,不要将《赵正书》关于胡亥合法继位的阐述予以大略否定。
[补记:文成许久,罕见知音。近才得读陈侃理师长西席《〈史记〉与〈赵正书〉——历史影象的战役》(《中国史学》第26卷,日本:朋友书店,2016年)一文,所论有可补充本文之说者,如所云“《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中与《赵正书》近似的部分笔墨并非《史记》原创,而是有所取材,与《赵正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等,读者可参看。]
作者简介:李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学术思想史。
[1]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2]按:柏人,《史记·秦始皇本纪》作“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台”,《赵正书》则当崩于柏人。沙丘,《史记·殷本纪》云纣王“广沙丘苑台”,《赵世家》曰“主父及王游沙丘”,沙丘当是一个广泛的皇家禁苑,其核心地区约在今河北邢台平乡,而柏人距平乡只有几十里,可能仍属沙丘范围。
[3]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189-190页。
[4]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190-191页。
[5]“李微”,《史记·蒙恬列传》作“李牧”。补记:刘乐贤指出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三年大将事(李)(微)”弩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六年代相剑也有“事”,可与简文相印证,并指出“牧”“微”古音附近;李牧名繓,王引之认为“繓”当为“棷”,古“藪”字。但他也谨慎地指出“微”或“”为“牧”通假字的说法还有待验证,“”为李牧其余一名或其余一字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备打消。拜会刘乐贤:《出土文献中的战国名将李牧》,《文物》,2020年第3期。按:“微”有贱义,“牧”有臣隶义,二者或也有字义关系。
[6]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191页。
[7]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192页。
[8]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193页。
[9]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194页。
[10]赵化成:《〈赵正书〉与〈史记〉干系记载异同之比较》,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300页。
[11]《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52、2553页。
[1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9页。
[13]《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1950页。
[14]李开元:《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45-149页。
[15]《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62页。
[16](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新序校释·善谋下》, 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75页。
[17]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公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页。
[18]康有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之说,或是依郑樵《通志·校雠略·秦不绝儒学论》之说而来。《史记·萧相国世家》说“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郑樵于是说:“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本也。”(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1页上)康有为遂谓萧何收得六经。
[19]廖平:《古学考》,《廖平选集》,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25页。
[20]蒙文通:《经学抉原》,《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57页。
[21](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册第1387页上;(元)方回:《续古今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2年,第853册第502页上。
[22](元)萧参:《希通录》,《丛书集成新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7册第416页下。
[23]《资治通鉴》卷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4页。
[24]拜会陈登原:《古今文籍聚散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6-41页。关于挟书律的内容,拜会李锐:《秦焚书考》,《人文杂志》,2010年第5期,第141-142页。
[25]《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2014页。
[26]蒙文通:《经学抉原》,《经史抉原》,第56-57页。
[27]蒙文通:《经学抉原》,《经史抉原》,第57页。
[28]《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第2568-2569页。
[29](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日]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7页。
[30]《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第2569页。
[31]拜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5期,第43页。“元年”前“以”字,据陈伟《〈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校读》补(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59,2015-06-14)。按:“(正)”字,看图版似没有;“箸”疑读为“诸”。
[32]拜会吴方基、吴昊:《释秦二世胡亥“奉召登基”的官府文告》,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25,2014-05-27;孙家洲:《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3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3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7页。
[35]高大伦:《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71页。
[36](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上篇,《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页。
[37]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3页。
[38]王叔岷:《庄子校诠》,第1336页。
[39](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上篇,《王弼集校释》,第80页。
[40]王志平:《也谈“铦”的“”》,中国古笔墨研究会、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古笔墨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11-619页。
[41]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1页。
[42](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67-468页。
[43]按:《忠孝》篇可能不是韩非的作品,拜会李锐:《再论商韩的人性论》,《江淮论坛》,2017年第3期。
[44](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43页。
[4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4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0页。
[47]《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7页。
[4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7-238页。
[4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7页。
[50]《史记·李斯列传》作:“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去世而不忘”(第2561页)。
[51]《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2页。
[5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1页。
[53]《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8页。
[5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1页。
[55]《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7页。
[56](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92页。
[57]《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2029页。
[58]《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73页。
[59]《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89页。
[60]雷依群也从继续制度、文化传统、治国理念和统治思想等方面论证扶苏不可能被立为太子,拜会雷依群:《论扶苏不得立为太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61]《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8、2552页。
[62]《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1950页。
[63]《史记》卷九九《叔孙通列传》,第2725页。
[64]《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第2568页。
[6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4页。
[66]《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8页。
[67]《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9页。
[68]《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1页。
[6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4页。
[70]徐仁甫:《史记表明辨正》,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1页。按:此则材料,为学生吴明明创造。
[7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4页。
[72]李开元:《秦谜:重新创造秦始皇·秦始皇的后宫谜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
[73]《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0页。
[7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2页。